礼宾服务的窗帘? - 彭博社
bloomberg
当玛丽·马丁在去年秋天89岁去世时,似乎标志着我在巴黎圣路易岛上租住的17世纪房子的一个时代的结束。作为这栋楼的门房35年,她在我们巨大的木门吱吱作响打开时透过拉开的窗帘窥视外面,并像罗马的守卫鹅一样对外人尖叫。视力的衰退结束了她的正式职责:分类邮件、擦洗楼梯、把垃圾桶推到外面。但她在她那间小小的一室公寓中仍然保持着象征性的权力,门房的巢穴就是这样称呼的。
这位典型的门房,尽管她的举止让人感到不适,却受到大楼里每个人的喜爱,似乎是我所认识的最后一位门房。就像法棍和三个小时的午餐一样,门房正逐渐成为一个消逝的法国机构。1950年的巴黎大约有60,000名门房在咆哮和闲聊。如今只剩下20,000人,预计到本世纪末这个数字将缩减到12,000人。他们的工作已被取代。如今,编码的键盘让租户在晚上打开外门,而不必叫醒门房。邮递员通常会分类邮件。而维护公司正在接管清洁工作。
因此,几周前,当一个年轻的新面孔出现在马丁夫人的窗前时,真是一个大惊喜:纳丁·达利尔——漂亮且渴望取悦他人。她自己也不太相信她在那里。“我真是太幸运了,”我们新的门房笑着说。“我希望我能在这里待到退休。”
幸运?住在一个10乘10英尺的房间里,地板粗糙,只有一盏荧光灯,一个简陋的淋浴,除了一个微波炉外没有任何烹饪设备?这样的居所会让任何人都感到不快——我也在想马丁的年轻继任者会发生什么。我还在想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门房。近年来,小时工已经很好地完成了马丁夫人的工作。
在她的新家里,达利耶坐在一张废弃的沙发上抽烟,她说她渴望一个门房的职位,因为在科西嘉酒店和巴黎住宅长时间的女佣工作后感到疲惫。尽管那些工作有些工资高出50%,偶尔还提供鱼子酱和熏鲑鱼,但“在40岁时,我想要平静和安宁。”她说。她似乎确实如此。每当我经过她的门房时,她都在看书或看电视。
至于我们为什么需要她,我问了雅克·巴科,一个为巴黎拍卖行评估古董的邻居,他还是我们25户合作社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门房就像是大楼的祖母,”他说。“她总是在那里,早上跟你说‘你好’,晚上回家时跟你说‘晚安’。”他喜欢有一个常驻的存在来筛查访客和处理紧急情况。达利耶的聘用没有异议。他说她“太年轻”,还没有获得“真正的门房精神”,但他认为她会的。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在1956年开始的三次巴黎之行中,我总共在这里生活了13年,经历了四位门房的统治。他们曾因我弄脏楼梯而责备我,曾对我的晚宴客人大喊大叫,还在我圣诞节只给他们100美元小费时抱怨。我曾把我的门钥匙留给他们以便朋友来访,但这是我能记得的唯一有用的服务。
改变的品种。然而,租赁代理说,门房为建筑增添了时尚,就像暴露的天花板横梁一样。时尚在圣路易岛上很重要,这里是一个价格不菲的17世纪住宅岛,位于巴黎圣母院后面。我们的建筑是一座酒店 particulier,一座石头豪宅,拥有宏伟的楼梯,是为路易十四的一位低级官员建造的。大多数公寓都豪华地配备了古董家具(有一个令人尴尬的例外——猜猜是谁的?)门房与装饰相得益彰。
但是尽管对旧巴黎魅力的怀旧,我已经了解到,巴黎传奇的门房正在发生变化。首先,不要称他们为门房,至少对年轻人来说。达利耶做了个苦脸:“门房是个老八卦,”她说。政治正确的称呼是 gardienne——或男性的 gardien,但几乎没有男性。而且他们也不全是法国人:法国超过一半的 gardiennes 是葡萄牙人。
更重要的是,gardiennes 已经成为一个组织良好的压力团体,以保护和改善他们日益缩小的职业。法国至少有五个门房工会——在政治和宗教信仰上各不相同——还有一个法律辩护协会。每月都有一本杂志《门房回声》,发行量为 15,000,里面充满了求职广告。工作机会稀少。
几周后,工会将开始与大型建筑的业主谈判新合同。薪资是议程的重中之重。他们希望将薪水从每月 1,275 美元(略高于最低工资)提高到 1,500 美元,适用于全职的 gardiennes。考虑到供需情况,他们无疑将不得不接受更低的薪水。像所有法国工人一样,门房将约 20% 的薪水投入养老金和健康计划,因此剩下的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必须支付小额租金以及水电费。
其他一些热门谈判问题包括:门房不再想清洗高于 5.5 英尺的楼梯窗户。“他们必须站在梯子上,可能会掉出窗外,”共产主义门房工会的秘书长珍妮娜·巴齐尔解释说。门房们还反对将纸和玻璃分开投放的生态趋势:这意味着每个早晨要拖更多的垃圾桶到人行道上。他们还希望取消周日早晨的垃圾收集,以便可以多睡一会儿。
老一辈的门房对这些担忧嗤之以鼻。“哦,天哪——他们现在的生活太轻松了,”90岁的凯瑟琳·马尔蒂内说,她作为门房工作了63年。在她的早年,马尔蒂内很少能睡得安稳,因为夜猫子租户在 sidewalk 上大声喊她的名字——这是规则要求的——让她来拉闩锁。她也没有白天的休息时间。现在,法律允许门房在中午和晚上8:30后拉下窗帘——这是一种不打扰的标志。马尔蒂内还厌恶她职业的新名称,一些老前辈说这个名称让人联想到牧羊犬。“我不是 gardienne,”她怒吼道。“我是门房!”
法国的这一特殊制度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的城堡有一个马厩管理员(comte de l’etable),负责照顾马厩,还有一个蜡烛管理员(comte des cierges),负责照看“蜡烛”——即室内。在拥挤的巴黎,只有像我这样的豪宅才能负担得起看护,直到19世纪中叶大型公寓楼开始兴起。拿破仑三世鼓励门房的普及,因为他们是很好的警察线人。在后来的反应中,1905年的法令禁止门房与邻里的仆人交谈,并声明“门房的所有闲聊都是严格禁止的。”
艰难的生活。我的新门房——抱歉,gardienne——说她赞同这种态度。“我天生就很谨慎,”达利耶说。“我照顾好自己,不会批评杜邦先生或杜朗先生”——这两个是法国的琼斯先生和史密斯先生的对应。
达利耶的生活很艰难,这也解释了她为何对新工作如此高兴。她的父母在她10岁时离婚并抛弃了她。作为青少年,她梦想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但在17岁时不得不辍学以养活自己。恋情也变得不顺。破产且失业,她通过一个天主教福利机构找到了新工作。
作为看护,达利耶可能会通过分析她的监护对象来满足她的精神病学倾向。然而,她的正式任务仅限于每天早上推三只垃圾桶进出,清理我们的院子,以及每周清扫四个楼梯一次。除此之外,她只需要在场,指引访客,接受包裹,并且——正如她最近所做的——如果有车堵住车道就报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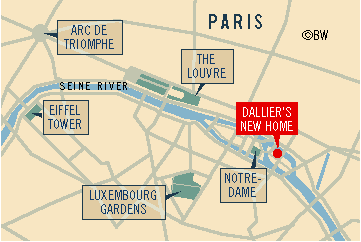 来自租户的圣诞小费和旧衣服将补充她微薄的工资。“也许我会在这个地方得到迪奥的裙子,”她沉思道。如果她有一天结婚,达利耶会把她的丈夫带进她的一间小屋。她已故的前任和她的丈夫曾在之前的一栋楼里养活了一个孩子。
来自租户的圣诞小费和旧衣服将补充她微薄的工资。“也许我会在这个地方得到迪奥的裙子,”她沉思道。如果她有一天结婚,达利耶会把她的丈夫带进她的一间小屋。她已故的前任和她的丈夫曾在之前的一栋楼里养活了一个孩子。
当我的新看护在橡木楼梯上扫地,并在鹅卵石院子里的马槽周围擦洗时,那些热爱旧巴黎魅力的人应该会高兴地看到年轻的血液进入这个濒危的机构。至于我,巴黎的魅力很好,但我希望小屋里的新女士能花很长时间来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