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官方上热爱仇恨美国人 - 彭博社
bloomberg
在我们在西安这个中国西北部的肮脏、污染严重的工业城市居住几个月后,我六年级的女儿阿里尔(11岁)从学校回家时怒火中烧:“我受够了!每次我们玩什么游戏,无论是团队运动还是单纯的摔跤,孩子们总是把它变成‘中国对美国’,而我总是美国。”
我并不感到惊讶。现在正在进行一项重大运动,旨在在阿里尔所在的学校中灌输爱国主义。在学校大门内,一张巨大的海报敦促学生“学习雷锋”,这位被誉为无私社会主义道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虚构英雄。阿里尔和她的同学们常常在午餐或放学回家的路上唱着血腥的爱国歌曲。
考虑到去年九月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紧张的关系,我们甚至很幸运能为阿里尔找到一所学校,尽管她流利地讲普通话,这个官方的中国国家语言。我们早在1991年和1992年就曾在中国生活过,那时没有任何问题。然而,那时我们在上海,经济繁荣正如火如荼。去年秋天回到中国时,我们发现西安的人们抱怨内陆地区被北京、广州,尤其是上海的繁荣所忽视。西安的平均工资徘徊在每月约50美元,甚至不到上海的一半。而商品的价格更高。一件优质的法兰绒衬衫要花费两周的工资;一辆单速自行车则需要一个月的工资。
我们回到中国是为了让我妻子在西安音乐学院担任六个月的富布赖特教授,教授大键琴和钢琴。我们一到那里,就发现政治环境完全不同。阿里尔申请附近高速大学附属的一所精英小学时被拒绝,校长粗鲁地告诉我们他“不能接收外国学生”。一位中国朋友解释说,校长担心如果让西方人与他的学生混在一起,会引发“官僚复杂性”。
排外阶段。在那时,我们本可以放弃,让阿里尔继续她从香港学校带来的工作。我回想起我们第一次在中国的经历,当时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警告我关于当地的教育。“他们会让你的女儿戴上红色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围巾,喊着毛主义口号,”他说。事实上,她在上海的经历非常积极,以至于我们希望她有另一个机会交中国朋友并继续学习语言。
幸运的是,阿里尔所在的我们居住附近的晓寨区学校愿意接收一个可能帮助他们六年级学生提高英语发音的学生。因此,阿里尔去了一个资金不足的学校,师生比例为58:1。至少那是一所学校。
我们很快了解到,第二所学校的友好只是个例,而早期的敌对态度则是典型的官僚行为。我妻子的音乐学院的官员干扰了她的讲座,并试图阻止她获得教职工住房甚至电话。我们花了将近两个月才获得居留许可,而这本应是例行公事。在她被邀请来教书和我们到达之间的一年里,气候发生了变化,至少在西安是如此。
敷衍的长篇大论。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中国陷入了自16世纪以来一直特征化的排外阶段。地方和国家报纸刊登评论,警告来自西方的“精神污染”。美国被指控试图“阻碍”中国的发展。官僚们,比如第一所学校的校长,觉得对美国人最好不要太友好——尽管他们对英国、比利时和其他外国国籍的人足够友好。没有官方的“对美国人强硬”政策,但在五十年的周期性共产主义反外来运动中,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对被视为敌人的过度友好可能会被用来反对他们。
然而,这次反美运动有所不同,至少在我们经历的过程中是这样。官僚们对此表示支持,但普通人却不然。对他们来说,意识形态已经死去,许多人公开对党表示蔑视。在西安,人们将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无能政策,而不是美国。对美国的最新指控——指责其鼓励台湾独立——并没有激起他们的反应。“我不在乎台湾人民做什么,”一位来自偏远村庄的农民说。“如果他们想独立,那是他们的事。”一位电子元件厂的工人也表示:“我关心的是有足够的钱为我的家人买食物,而这变得越来越困难。”
有时,甚至连政府也忽视自己的反美运动,这也是国旗挥舞没有流行的另一个原因。虽然北京指责美国进行经济破坏行为,比如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它却乐于与希望投资从飞机制造厂到长江大坝的美国人达成交易。一位在西安的美国航空航天高管说:“当我们与某个部门的人开会时,他们会先发表一番攻击美国的演讲,例如指责美国允许台湾总统访问美国,然后他们会歉意地微笑,我们就开始谈正事。我们都明白这只是他们必须做的事情。”
在我在西安的几个月里,只有一次听到对美国的直接批评。一位出租车司机,前人民解放军士兵,指责美国阻碍中国的现代化。“我在我们的报纸上读到的,”他说,耸了耸肩。更常见的是,工人和农民似乎已经善于从媒体的字里行间中解读,带着感情和钦佩谈论美国,但批评自己的政府和共产党。
肥猫。“领导们应该被排成一排,枪毙,”一位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的被裁员工人说。在我早些时候在上海的逗留期间,大多数批评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出现。一句流行的笑话是:江泽民的司机在路口问中国总统该往哪个方向转。江泽民回答:“左转和右转。”
如今,这种幽默缺失,愤怒却是纯粹的。即使是富裕的人也对政府官员和党棍的干预感到不满。“你无法想象我因为政府官员的骚扰而差点不得不关门的次数,”一位餐馆老板抱怨道。
这次腐败现象更加明显,这可能是公众愤怒的主要原因。梅赛德斯-奔驰、宝马,甚至劳斯莱斯的豪华轿车,大多数都挂着官方牌照,挤满了五星级酒店和高档餐厅的停车场。在里面,军方高层和党领导人进行着老百姓称之为“吃得多,喝得多”的活动。
政府似乎不理解这种怨恨。北京的宣传部显然认为西安的居民——许多人失业,孩子们在拥挤、没有暖气的教室里——会对电视上频繁播放的沿海城市的新桥和繁忙的生产线感到爱国自豪。西安的观众不仅因为嫉妒而抱怨,还因为他们宁愿收看《海滩救护队》。
虽然城市领导尽力现代化西安并吸引投资,但他们的努力却在与广泛的愤怒赛跑。历史上,西安及其周边贫困的陕西省一直是叛乱的中心。例如,在1989年,当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挤满学生时,西安的街道上也挤满了抗议腐败、独裁和无能的学生和工人,持续了数周。许多人说,自那时以来,问题加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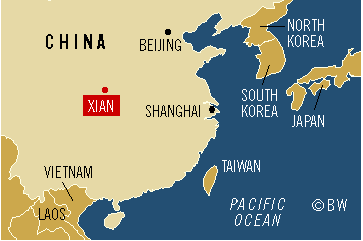
 在六年级水平上,通过使用反美、反西方的宣传来重新引导愤怒和挫折的努力仅取得了名义上的成功。中美之间的游戏并没有影响我女儿与学生和教职员工建立亲密友谊的能力。而民族主义运动可能已经帮助孩子们变成了11岁的愤世嫉俗者。当当地电视新闻团队拍摄早晨升旗仪式时,阿里尔接受了采访。当被问及她对中国的看法时,她回答:“中国非常有趣。”一位同学意味深长地对她眨了眨眼,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回答。”
在六年级水平上,通过使用反美、反西方的宣传来重新引导愤怒和挫折的努力仅取得了名义上的成功。中美之间的游戏并没有影响我女儿与学生和教职员工建立亲密友谊的能力。而民族主义运动可能已经帮助孩子们变成了11岁的愤世嫉俗者。当当地电视新闻团队拍摄早晨升旗仪式时,阿里尔接受了采访。当被问及她对中国的看法时,她回答:“中国非常有趣。”一位同学意味深长地对她眨了眨眼,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