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滥用 - 彭博社
bloomberg
灯光昏暗,音乐柔和浪漫。那是去年六月Astra USA Inc.全国销售会议的最后一晚,几对员工在波士顿郊区一家酒店的舞厅里跳舞。Astra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拉尔斯·比尔德曼,当时49岁,正与一位25岁的销售代表帕梅拉·L·佐特曼纠缠在一起。两名旁观者注意到,比尔德曼醉得厉害,正用手抚摸她的背部,并在她的脖子上轻咬。
突然,佐特曼冲进了附近的洗手间。她哭泣着告诉那里的其他女性,比尔德曼试图吻她。佐特曼在公司工作不到一年,显然没有得到在场两位资深女性经理的多少同情。根据佐特曼后来向两个消息来源提供的说法,这些女性实际上告诉她:“这就是Astra的情况,你最好习惯它。”
不再如此。4月29日,当《商业周刊》即将发布对Astra性骚扰指控的六个月调查结果时,比尔德曼被暂停职务,并被Astra的母公司、瑞典大型制药公司Astra AB解除责任。母公司任命其最资深的高管之一扬·拉尔松接替比尔德曼,并聘请外部律师进行彻底调查。
Astra的高级管理人员承认,《商业周刊》的调查引发了这一突然行动。尽管比尔德曼几个月前就已告知上级有关调查的情况,但瑞典Astra执行委员会成员卡尔-古斯塔夫·约翰松表示,公司在4月19日收到《商业周刊》的一封长信之前,并不知道指控的全部范围。“我们没有听到过如此详细的信息——当然也没有听说比尔德曼本人是某些指控的焦点,”约翰松说。对于Astra自己初步调查的进一步评论——其中也包括对比尔德曼轻微财务不当行为的指控——约翰松表示,Astra暂停了其美国首席执行官,因为“我们对他失去了某些信任。”
《商业周刊》的调查涉及对70多名前任和现任员工的采访,揭示了在比尔德曼担任阿斯特拉美国首席执行官的15年间,令人不安的投诉模式。《商业周刊》发现了十几起女性声称她们被比尔德曼或其他高管性骚扰或索要性服务的案例。许多女性描述了她们被期望陪同高级管理人员前往酒吧和舞厅的晚上。其他人则频繁收到邀请,加入那些常常酩酊大醉的经理们在酒店套房中进行更亲密的深夜聚会。直到最近,公司聚会都是喧闹的场合,几乎强制要求大量饮酒和跳舞。“大家被鼓励尽可能喝醉——并对女性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前阿斯特拉销售代表金伯利·A·科特回忆道,她在1994年获得了一项骚扰指控的庭外和解。“如果他们想抓住一个女人的胸部或屁股,那是可以的。”
甚至许多男性员工也感到震惊。“我从未见过如此明显和不当的行为,”阿斯特拉代表马沙安·盖伊说,他在1992年辞职,因为他不喜欢这种文化。尊敬的地区销售经理大卫·G·瑟斯顿补充道,他在去年九月因厌恶而辞职:“如果有哪家公司性骚扰猖獗,那就是这里。”
比尔德曼和阿斯特拉美国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两周内未回应《商业周刊》多次请求采访。5月1日,当文章即将出版时,比尔德曼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明确否认了这些指控。比尔德曼的律师声称他的客户没有足够的时间回应。在比尔德曼被暂停前一周的初步采访中,阿斯特拉美国的总法律顾问查尔斯·E·杨和全国销售经理罗伯特·沃戈尔强烈否认了过度饮酒和广泛性骚扰的指控。然而,杨拒绝谈论已解决的投诉,并拒绝回应众多具体指控。现在,随着来自瑞典的高管接管调查,约翰逊表示他无法评论早期的否认是否仍然有效。
一些个别指控可能难以确凿证明。这就是性骚扰的本质,部分是一个感知的问题:一个女人认为是无害的玩笑,另一个女人可能会觉得极其冒犯。此外,一些事件发生时只有被指控的骚扰者和他的指控者在场。但在许多情况下,阿斯特的指控骚扰是由不止一个人目击或在一个晚上由不止一个女性经历的。而且,围绕同一男性高管的投诉数量之多,以及现任和前任员工普遍认为环境对女性普遍敌对的观点,表明阿斯特存在严重问题。
阿斯特的例子恰逢三菱汽车制造公司在伊利诺伊州诺马尔工厂的性骚扰丑闻。那里,15名女性指控她们被摸索并遭受贬低和冒犯的评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对该公司提起了其最大规模的此类诉讼,指控三菱未对重复的投诉做出回应。三菱否认不当行为,并且至少在最初时,发起了一场激进的公关活动,旨在表明其员工对EEOC的指控表示异议。
虽然三菱和阿斯特因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显得格外突出,但许多公司正在努力应对性骚扰的指控。自四年前安妮塔·希尔在克拉伦斯·托马斯确认听证会上提出挑战以来,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激增,向EEOC的投诉数量已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5,549起,而金钱赔偿则增加了三倍多。作为回应,许多雇主已引入敏感性培训并制定了处理投诉的明确政策。
性骚扰到底是什么?EEOC 指南将其定义为工作场所中“不受欢迎”的性关注。在极端情况下,这意味着要求或暗示将获得工作福利以换取好处。但联邦法律也禁止任何造成“令人恐惧、敌对或冒犯性工作环境”的行为。
涓滴效应。关于阿斯特拉,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所指控的骚扰是从高层发出的,然后在组织中蔓延。许多感到尴尬和愤怒的女性仍然遵循了子公司首席执行官设定的不可接受的行为标准。她们的男性同事也是如此,许多人后来表示,他们也认为阿斯特拉的行为令人反感。
正如阿斯特拉案件所暗示的,少有人有勇气或经济能力去揭发这种情况。一些阿斯特拉员工因担心与一家财力雄厚的公司对抗而感到畏惧——尤其是那些投诉的人声称他们遭到了报复。经济需求意味着其他人忍受了他们认为是贬低的行为。许多被采访者还表示,他们担心投诉只会导致被视为麻烦制造者——这在就业市场上会困扰他们。“如果另一家制药公司知道你参与了这样的事情,你被雇佣的机会就微乎其微,”1991年离职的前代表玛丽·安·洛说。“而且,这非常个人化。没有人想公开性骚扰。你知道如果这事上了法庭,你会被审判,而不是骚扰者。”在高层默许的情况下,许多感到被骚扰的女性——以及同情她们的男性——干脆选择了辞职。
法律威慑在哪里?前员工表示,在许多情况下,当女性有骚扰或报复的证据并威胁提起诉讼时,阿斯利康为了避免法律制裁而达成和解。根据《商业周刊》所知,它已向五名女性支付了从20,000美元到约100,000美元不等的现金。作为交换,这些女性同意保持沉默。“当女性不愿退让时,他们就会给她们赔偿,”前地区经理索斯顿说。因此,对于那些被指控骚扰的高管来说,没有真正的惩罚。更糟的是,他们似乎利用股东资金来保护自己。
约恩否认阿斯利康支付女性以换取她们的沉默。阿斯利康表示,只有少数和解案例,而且大多数索赔来自因表现不佳而被解雇的人。尽管它表示大多数索赔是毫无根据的,但它坚持认为和解主要是为了避免昂贵的诉讼。从外部来看,阿斯利康似乎有着良好的记录。该公司表示,它赢得了唯一一个进入陪审团的骚扰案件,自1990年以来在马萨诸塞州的档案中只有一起严重投诉。至于EEOC,阿斯利康表示它只面临过四起索赔,其中两起仍在进行中。
军事化。内部人士将骚扰环境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归咎于比尔德曼,这位在阿斯利康工作了22年的老员工。这位出生于瑞典的高管自1980年代初以来一直负责美国分部,并因其财务成功而受到赞誉。“他是一个非常有纪律、以目标为导向的人,”斯特凡·索尔维尔说,他曾是阿斯利康美国的第二号高管,直到去年辞职去经营另一家公司。公司在马萨诸塞州韦斯特伯勒的校园式总部,员工人数已增长到1,500人,收入达到3.23亿美元。其产品包括局部麻醉剂Xylocaine和过敏药物Rhinocort。一种新的哮喘药物Pulmicort预计将很快上市。与此同时,比尔德曼在瑞典的上司们也推动了快速增长:母公司阿斯利康去年销售额达到53亿美元,是1991年的三倍。
瘦高,长发,蓬松的胡子和锐利的眼睛,比尔德曼是一个有魅力的,虽然有些古怪的领导者。他喜欢穿着不寻常颜色的西装:紫色、珊瑚色或交通锥橙色。那些为他工作过的人形容比尔德曼对青春、美丽和健康有着执念。他也喜欢奢华的生活。根据马萨诸塞州的记录,他的六辆车中包括一辆1967年的兰博基尼Miura和一辆1967年的法拉利GT。已婚,有孩子,内部人士说他是鱼子酱、优质葡萄酒和香槟的鉴赏家。
许多消息来源称,在阿斯特拉,比尔德曼是一个独裁者。他在阿斯特拉简朴的办公室里建立了一种严格、几乎是军事化的氛围。大多数员工每天都必须在同一时间去午餐,并且必须获得许可才能在他们的隔间墙上挂任何个人物品。另一个奇怪的规定是:除了最高级别的高管,所有人都必须使用一个集中传真号码,许多前内部人士表示,比尔德曼会收到所有进出信息的副本。“他对公司有完全的控制;每个人都害怕他,”一位两年前友好离职的前经理说。
许多消息来源称,比尔德曼会以任性的方式行使权力。一位销售代表回忆说,在一次会议上,比尔德曼不喜欢一位高管穿的西装,并告诉他换掉。那位高管迅速服从。比尔德曼还坚持其他关于着装的奇怪规定,包括一项要求在所有公司活动中必须佩戴阿斯特拉徽章的规定。忘记佩戴徽章的人会受到严厉的训斥。“我以前常常随身携带额外的徽章,”一位前经理说。“这种恐惧变得如此失控,我记得至少有六次我给别人一个额外的徽章,他们因为丢失自己的徽章而感到非常震惊。”
阿斯特拉之路。为了推动其快速增长,自1980年代末以来,阿斯特拉雇佣了数百名年轻的销售人员,包括男性和女性。许多消息来源称,对于女性招聘者来说,外貌似乎显得格外重要。一位今年早些时候辞职的男性销售代表回忆起两位高级男性经理要求他帮助说服一位犹豫不决的候选人加入公司的经历。“他们明确告诉我为什么想要她被录用——因为她非常有吸引力,”他说。另一位前经理回忆起乔治·罗德曼,当时负责阿斯特拉增长最快的部门的副总裁,拒绝了一位不吸引人的候选人,称:“我们不录用她。我无法想象和她坐在酒吧里喝酒。”在比尔德曼暂停之前的采访中,阿斯特拉的全国销售经理沃戈尔否认外貌在选择中起任何作用。罗德曼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否认了他行为不当的指控。他表示自己确实有饮酒问题,但他已经自愿接受了咨询,并且自1994年以来在阿斯特拉的活动中没有饮酒。
对许多招聘者来说,这份工作是梦想成真。销售药品是一项高薪且备受追捧的职业。起薪为35,000美元,加上汽车和丰厚的奖金,阿斯特拉的薪酬比大多数竞争对手更好。但在外出实地工作之前,新聘的销售代表——其中很少有人有药品销售经验——参加了阿斯特拉为期九周的严格培训课程,课程内容包括深入的销售指导以及解剖学和生理学等科目。培训生必须努力学习,并且经常接受测试。
培训还提供了对阿斯特独特文化的沉浸体验,这被称为阿斯特方式。每班最多有100人,在阿斯特总部附近的西博罗万豪酒店住宿,为期九周。公司只支付了一张回家的机票,并不鼓励学员进行其他旅行或接待访客。学员们很快了解到,阿斯特方式包括一套严格的规则,涵盖从销售技巧——演示必须记忆并几乎是机械地向医生呈现——到可接受的休闲着装。(不允许穿牛仔裤。不允许穿短裤。必须穿袜子。)一些规则看起来微不足道。其他规则则为新员工增添了光彩。学员们被教导如何以欧洲风格使用餐具以及如何饮用葡萄酒。
经历过培训的数十个来源将其描述为全面而孤立。与家人和朋友隔绝,如果他们未能迅速适应这些广泛的新规则,常常会受到训斥,许多人表示阿斯特的培训与军事基础训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些新员工甚至被穿着运动服在大楼内游行一天,管理人员穿着迷彩服大声提问。那些回答错误的人必须做俯卧撑。其他人补充说,这几乎就像一个邪教。“他们告诉你如何吃、喝和睡,”去年辞职的阿斯特代表克里斯蒂娜·K·贝尔说。“这是一种非常控制和专横的氛围——就像阿斯特拥有我一样。”
开放酒吧之夜。社交似乎在阿斯特方式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新员工们一次又一次被告知,要成功,他们必须努力工作,也要努力玩。“工作八小时,玩八小时,睡八小时,”这是比尔德曼和其他高管经常使用的一句话。“成为成功代表的一部分就是要与客户在一起——不仅仅是朝九晚五,”前第二号人物索尔维尔解释道。“这意味着要进行娱乐。”
当然,良好的社交技能是许多销售工作的关键。但在经理们每周举办三到四次的开放酒吧之夜,吸引人的女性的社交技能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高层管理几乎没有关注男性学员,但他们对女性学员却非常关注,”1993年的培训生肯德拉·库尔茨说,她在一年后离开了阿斯特拉。约恩和沃戈尔否认社交或饮酒在阿斯特拉扮演了不当角色。
尽管如此,来自四个不同班级的培训生表示,酒吧之夜很常见——而比尔德曼和罗德曼是常客。“比尔德曼会参加会议,”一位因环境而在1993年离开的前代表回忆道。“他会在大家之后去酒吧。”许多人表示,罗德曼经常会在酒吧待到深夜——并施压其他人也这样做。
种族问题。经常,罗德曼和其他经理会叫女性培训生到他们的房间,邀请她们下酒吧。这种邀请很难拒绝。根据最近退休的阿斯特拉培训总监特伦斯·利希的说法,大约15%的新员工在培训期间被解雇。参与者表示,他们被反复告知社交技能是评估的关键。此外,待在酒吧的经理们可能会影响被分配到旧金山或北达科他州法argo的机会。“你必须去酒吧,”一位仍在公司的女性代表说。另一位去年辞职的女性补充道:“他们会利用他们的权力和权威让你觉得如果你不配合就没有工作。”
实习生们表示,他们经常对酒吧里发生的事情感到冒犯。1992年末接受培训的黑人女性莱莉亚·布什说,罗德曼多次在她的房间里叫她,邀请她和他一起去酒吧。她和另一位黑人前代表科迪莉亚·E·韦布(也已提交EEOC投诉)声称,罗德曼喜欢谈论性别中的种族差异。“他说黑人女性在性方面比白人女性更像种马,”布什指控。“他说他是一个白人身体里的黑人男人。”两位女性的解雇情况存在争议。
比尔德曼、罗德曼和其他经理们还会邀请女性外出进行更亲密的活动。在多次拒绝他后,库尔茨回忆起最终同意参加比尔德曼组织的与六名实习生(四名女性和两名男性)一起的夜晚。爱德华·阿伦斯,一位负责机构业务的高级执行官,也加入了他们。晚餐后,团队来到一个昏暗的钢琴酒吧,比尔德曼点了舞蹈和香槟。实习生贝尔记得这是一个“搭讪”的酒吧,“那种地方你会遇到某人,进行一场热烈的舞蹈,然后回家。”
当聚会转移到一个喧闹的夜总会时,贝尔记得阿伦斯“在我身上摸来摸去”,并指控这两位高管“与我跳得非常近。我一直在想:‘我该如何逃离这里?’”她说。在一份书面声明中,阿伦斯否认他曾骚扰过任何女性,称这些指控“完全是虚假的。”
该小组在凌晨2点后返回西博罗万豪酒店。尽管比尔德曼住得很近,但他还是租了一个套房过夜,并希望大家都能加入他。“我们不想上去,”贝尔说。“但我们觉得应该露个面。”只有库尔茨悄悄溜走了。
楼上,饮酒和跳舞继续进行。“我觉得我不能说不,”贝尔说。比尔德曼跳舞“太靠近”了,她声称,并不断把她引导到床附近。当比尔德曼评论她似乎很紧张时,她告诉他她感到不舒服。比尔德曼的回应是:“我们在阿斯特拉这里非常开放。”在她逃到沙发后,贝尔声称比尔德曼过来“把手臂环绕着我,把我拉向他。我一直在想:‘他是公司的总裁。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引人注意地摆脱这个?’”
不久之后,贝尔搬到了她在辛辛那提的新区域。在与她的新经理瑟斯顿的第一次会议上,她开始哭泣并告诉他整个故事。他代表她提交了一份正式的骚扰投诉。阿斯特拉的约翰说,公司进行了调查并得出结论,贝尔的指控没有依据。他说,调查涉及对其他五名实习生进行宣誓陈述。“其他五个人,”他说,“发誓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不当行为,没有任何冒犯。”
但是阿斯特拉似乎进行调查的方式引发了质疑。首先,比尔德曼直接参与了。不久之后贝尔提交投诉,她说比尔德曼打电话给她在酒店的房间。贝尔回忆说:“拉尔斯对那晚非常担心。” “他问我:‘我觉得我的工作有危险吗?我感到有压力吗?’”贝尔说,比尔德曼甚至告诉她不要告诉瑟斯顿他打过电话。贝尔说,很明显,比尔德曼“是在试图保护自己。”
不久后,在一次全国销售会议上,库尔茨被叫出会议并被引导到比尔德曼的顶层酒店套房。“这非常令人畏惧,”她回忆说,“只有我和拉尔斯。”在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中,她说比尔德曼告诉她他要解雇另一个公开追求骚扰投诉的人。然后,他把她引导到另一个房间去见约翰,公司的总法律顾问,并签署一份关于晚餐和舞会的宣誓书。库尔茨说,宣誓书仅仅说明她在那晚没有受到比尔德曼的骚扰。“他们在提问时非常小心,”库尔茨说,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签字。“很明显,他们是在试图保护拉尔斯。”
在培训期间,少数女性抗议这种待遇。大多数人都在二十多岁,Astra是她们大学后的第一或第二份工作。“人们缺乏经验,”1991年离开的安·玛丽·诺瓦克说。“他们并不知道在商业环境中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
还有一些人说,她们认为投诉等同于辞职。在新工作开始几周后,大多数人并不准备这样做。“我一直告诉自己:‘培训只有两个月,然后我就可以出去工作,’”一位前代表回忆道。
当然,一些对高管冷淡的女性发现,她们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有一些人公开回应来自高级管理人员的关注。有些人天生就很会调情,享受派对的氛围。也许有些人希望通过老旧的“试镜沙发”传统来改善自己的职业生涯。在Astra内部,这些女性被称为“被选中的人”。培训结束后很久,她们经常被看到与高级管理人员一起参加晚宴和其他公司活动。沃戈尔坚持认为,和比尔德曼坐在一起的代表是“严格根据表现选择的”。
但是那些认为骚扰会随着培训结束而停止的人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对于其两个主要部门,Astra每年举行三次全国销售会议。由于比尔德曼和其他高管通常参加每周的为期一周的会议,醉酒的派对和骚扰再次开始。“我收到包裹时,就开始感到恶心,”韦伯说。
热情的派对往往变得喧闹。在一次劳德代尔堡的会议上,数十名穿着晚礼服的男性和女性最终落入酒店游泳池。许多人那晚最终睡在游泳池的躺椅上。在1991年于纽约州上州的独家萨加莫尔度假村举行的另一场会议上,几位在场的人表示,派对失控到人们把碗碟扔出窗外,烧毁壁炉里的家具。酒店经理在威胁报警后,团队第二天早上退房。“他们的行为令人难以置信地不专业,”一位酒店官员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公司团队。”
在其他会议上,许多深夜活动发生在仅限邀请的经理套房派对上。米歇尔·波特,一位1991年离开的前代表,回忆起曾参加过比尔德曼的一个派对。在吃喝了很多之后,波特在其他人都离开时也准备离开。比尔德曼让她留下,然后他躲进了另一个房间。“突然间,他穿着浴袍出来,”她回忆道。“我说:‘我想离开。’他抓住我的手臂,说:‘我想和你谈谈。’”波特迅速离开了。
“这个是我的。”埃德·阿伦斯是许多投诉的另一个对象。在1993年销售会议的一个深夜派对上,韦布回忆道,阿伦斯在走廊里抓住她的脖子,试图吻她,并大声喊道:“手放开。这个是我的。”她说,阿伦斯“满身酒气。我一直在想:‘我得离开。’”但当她试图离开时,阿伦斯变得好斗,并责骂她的经理允许她离开。在他的书面声明中,阿伦斯否认自己醉酒或试图吻韦布或以任何方式骚扰她。
尽管阿斯特拉的母公司坚称不知道其美国子公司的情况,但许多消息来源表示,当欧洲人从总部访问时,他们也卷入其中。1992年的实习生丽莎·D·霍尔回忆说,罗德曼让她去酒吧招待来访的高管。“这些都是副总裁,高层人士,”霍尔说,她是一位1994年因两次请病假而离开的黑人前代表;具体情况存在争议。“罗德曼告诉我对他们要友好。”她说,瑞典人“喜欢黑人女孩。”
几个人还记得1994年阿斯特拉德国子公司总裁安德烈亚斯·费尔纳的访问。一位前代表说,在一个晚会上,费尔纳从她身后走来,“抓住我的屁股,把我拉向他。他说:‘我想让你过来和我坐在一起。’”她说她之前从未见过费尔纳。那天晚上,在被迫与他合影后,前代表韦布声称费尔纳“试图把他的房间钥匙放到我的手里。他告诉我在那等着。”韦布说她拒绝接受钥匙。费尔纳否认所有指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从未抓过任何女性……在屁股上,”他在书面回应中说,并补充说他也没有要求任何女性与他一起去他的房间或给她们他的钥匙。
痴迷。韦布说她后来告诉她的经理关于这一事件,并要求他提出投诉。她说他同意这样做,但“他说很多人过去也提出过投诉,但没有效果。”她说她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她投诉的任何消息。
尽管对性痴迷的影响在培训和销售会议期间最为强烈,但前员工表示其影响遍及整个文化。几位前男性经理表示,曾是比尔德曼宠儿的女性通常会直接与他打交道,而更高级别的男性经理很少与首席执行官交谈。其他人则表示,他们不敢惩罚与高层有联系的落后女性代表,担心失去自己的工作。“如果你所在地区的某人和拉尔斯关系密切,那就不要碰,”一位最近离开的老内部人士声称。
许多来源还认为,身体吸引力或与高层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女性似乎获得了更大的奖金,并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得更好。例如,布什在她的EEOC申诉中抱怨说,她因表现不佳而被解雇,而另一位销售业绩更差的女性代表却被保留。布什声称,这位代表与一位区域经理有染。在她的EEOC申诉中,韦布指控她在培训期间的室友与罗德曼有染。这位女性后来成为她班级中首批晋升为地区经理的人之一。尽管几位代表表示这位女性表现良好,可能值得晋升,但偏袒的印象依然存在。
还有其他问题。考虑到高层的信号,一些低级别的男性经理据称将其视为以类似方式行事的许可。在1992年末金·科特开始在波士顿地区工作后,她的当时经理马克·霍兰兹开始在她巡回时乘坐她的车。她声称霍兰兹会不当触碰她,并讲述他所读的淫秽小说中的场景,暗示科特“可以很好地融入这个”场景。尽管他在面对面时赞扬她的表现,科特声称,当她没有回应时,霍兰兹开始在书面评估中批评她。当她没有收到她之前所承诺的加薪时,科特表示她最终与霍兰兹对峙。根据科特的说法,霍兰兹回应说:“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打算怎么做?”科特的反应是:“我说:‘我不打算和你上床。’”在一份书面声明中,霍兰兹宣称对这些指控“绝对和完全否认。”
Cote说她向Vogel抗议,但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她投诉的任何消息。Vogel同意Cote提出了投诉,并表示他按照Astra的投诉程序进行了调查。在采访了Hollands和Cote后,他表示他将投诉转交给人事部门,Cote的指控被发现“没有现实基础”。然而,Vogel承认他只是给人事部门打了电话,从未提交书面投诉。他也没有进一步与Cote交谈或跟进。她在两个月后以有争议的条件离开了公司。Cote在1994年与Astra达成部分和解,并在4月29日对Hollands提起了后续诉讼。
当然,许多其他低级别的男性经理对这种行为感到震惊。然而,他们面临的难题是该怎么办。前代表Mashaan Guy表示,如果他看到一位女性处于尴尬的境地,例如,他会加入谈话。他还建议女性如何转移注意力。但这种文化让他感到愤怒,以至于他最终辞职。“几次,我想揍其中一个家伙,”他说。“作为一个男人,我感到无能为力和尴尬。”
前经理Thurston表示,他和一小群男性经理经常讨论骚扰对士气的影响。部分原因是,他们也担心自己的声誉:他们害怕Astra的所有男性都会被贴上骚扰者的标签。最后,Thurston表示他找到了他的老板Vogel,并告诉他骚扰正在伤害公司。但Thurston表示,男性经理几乎没有能力推动改变。“你想说的是:‘Lars,保持你的裤子,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他说。“但你不能这样做。这是一家完全专制的公司。Lars说什么,就是什么。”Vogel否认Astra存在任何普遍的骚扰问题,或任何经理曾与他谈论过此事。
随着大多数女性代表在外工作,总部的明显问题减少了。但对女性的类似态度似乎依然存在。一个显著的例子是:1991年初,在大楼内分发的一本光鲜亮丽的日历,名为《阿斯特拉魅力女孩》。它展示了办公室员工以挑逗姿势的照片,配有化妆、华丽的衣服和诱惑的眼神。四位相关人士,包括拍摄这些照片的摄影师表示,这本日历是作为礼物送给比尔德曼的,尽管阿斯特拉否认这一指控。
受压制。反对阿斯特拉气候的女性很快发现自己的行为受到审查。在日历发布约一年后,其中一位女性,南妮特·科尔科兰,向马萨诸塞州反歧视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性别歧视投诉,声称“阿斯特拉的女性一直遭受性骚扰。”作为回应,阿斯特拉否认科尔科兰曾遭到骚扰。相反,公司指责科尔科兰所谓的“不当和不专业行为。”在一起事件中,阿斯特拉表示,“有报告称科尔科兰在培训结束后会与各种[实习生]社交,”并且她曾在自己的公寓举办过一个聚会,期间“酒精消费过量——因此发生了两名实习生之间的争吵。”
确实,有大量证据表明,提出骚扰投诉的人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受到压制或成为解雇的目标。在1991年9月的一次销售会议上,一位名叫毛拉·林奇的波士顿地区代表召集了一次女性代表的非正式会议,讨论改善阿斯特拉敌对环境的方法。高层管理很快得知了这次会议,林奇,这位担任代表已有数年的女性,突然受到关注。根据接近林奇的人士说,她的经理开始进行突击检查,并对小事挑剔。到12月,他表示她必须离开。她雇了一位律师向MCAD提交投诉,但阿斯特拉迅速达成和解。她也签署了保密条款。女性小组再也没有开过会。
破坏计划。或许最严重的所谓报复案件源于1993年末一起涉及年轻实习生劳拉·摩尔的事件。根据熟悉情况的人士透露,摩尔声称有一天晚上,罗德曼在酒店酒吧找她,并邀请她去另一家酒吧。由于害怕拒绝,她带上了两个男性朋友。罗德曼在从酒吧回来的车上 allegedly 对她表现得很亲密。摩尔在午夜过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告诉朋友,罗德曼敲了门并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房间。尽管她一再要求他离开,但他 allegedly 将她按在墙上并吻了她。他还 allegedly 要求她和他一起睡。熟悉这一事件的人说:“罗德曼真幸运没有被叫警察。”
摩尔最终把罗德曼赶出了她的房间,并立即打电话给她即将被分配的区域经理詹妮弗·普赖斯。普赖斯是一位从阿斯特拉外部聘请的经验丰富的经理,她同意积极追查投诉。比尔德曼再次参与了调查。他询问的其中一位是库尔茨,摩尔的朋友和同事。“拉尔斯告诉我……他担心詹妮弗·普赖斯有一个破坏公司内部人员的计划,”库尔茨声称。“拉尔斯告诉我他打算解雇詹妮弗。”
不久之后,普赖斯被解雇。官方理由是:表现不佳。普赖斯坚信她是因为报复而被解雇,威胁要起诉。公司迅速达成和解,以换取普赖斯的沉默。阿斯特拉拒绝讨论有关普赖斯的指控。
在过去的18个月里,阿斯特拉已经收敛了其喧闹的文化。现在,销售代表在会议上发放有限数量的饮料券,最近的培训课程也变得安静了许多。但酗酒仍然是常态——而当酒水流动时,旧阿斯特拉的风采依然显露无遗,正如去年六月与佐特曼的事件所示。
此外,在比尔德曼被迫停职之前,阿斯特拉继续否认存在任何问题。在与《商业周刊》的初次采访中,约恩展示了一群主要是低级别的女性员工。她们的故事在三名阿斯特拉法律代表和两名外部公关高管在场的情况下,完全与多位独立来源向《商业周刊》所述的情况相矛盾。这些努力似乎是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抹黑《商业周刊》的文章以及那些提出骚扰指控的人。事实上,在阿斯特拉高管在一月中旬意识到调查后,公司要求女性销售代表签署一封信,否认她们曾见过或经历过任何骚扰。表面上看,这是由忠诚的女性销售经理组织的草根努力,但内部人士表示,许多员工相信这一行动源于高层的恐慌。大多数女性签署了;一些人担心如果不签署会失去工作。
尽管许多遭受阿斯特拉骚扰最严重的女性已离开公司,但一些人仍因经历而受到伤害。突然离开阿斯特拉往往使得寻找另一份工作变得困难。潜在雇主总是询问她们为何离开。“这很困难,因为你想告诉他们在阿斯特拉发生了什么,但你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理解,”库尔茨说。在一次面试中,库尔茨表示,她告诉了女性面试官她的一些故事。“你可以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库尔茨说。“她在想:‘丑闻,离我们远点。’”许多人表示,她们为了找到工作而谎称离开的原因。
一些人声称他们仍然遭受心理创伤。前代表伊冯娜·斯托克斯表示,极度的压力和性骚扰的结合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有一天她在给医生打电话时开始哭泣。医生将她转介给了一位精神科医生。她仍在服用抗抑郁药,她说:“我只想重新做我自己。我回想起来说:‘我怎么能让这家公司这样对我?’”
韦布声称阿斯特拉把她从一个快乐无忧、深信宗教的年轻女性变成了一个情绪崩溃的人。她说,长达两年半的骚扰造成的伤害如此严重,以至于她的头发开始脱落,常常感到恶心,并且开始抓挠自己的背部和胸部,直到皮肤变得红肿。她的医生在去年五月要求她休病假,她仍在接受精神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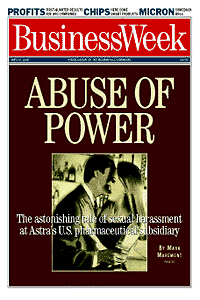 在休假近一年后,韦布对正常日常事件的感知仍然受到她在阿斯特拉经历的扭曲影响。作为她教堂合唱团的常客,韦布说:“当我觉得教堂里的人拥抱我不对时,就有些不对劲。”在最近的一次工作面试中,她说男面试官问了她一个完全无辜的问题:她是否愿意出差?但韦布说她的本能反应是:“他想把我带进酒店房间。”韦布说,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是几个月前阿斯特拉终于解雇了她。现在她正在准备提起诉讼,她发誓:“如果我必须失去我所有的钱,我也会这样做,以向他们证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在休假近一年后,韦布对正常日常事件的感知仍然受到她在阿斯特拉经历的扭曲影响。作为她教堂合唱团的常客,韦布说:“当我觉得教堂里的人拥抱我不对时,就有些不对劲。”在最近的一次工作面试中,她说男面试官问了她一个完全无辜的问题:她是否愿意出差?但韦布说她的本能反应是:“他想把我带进酒店房间。”韦布说,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是几个月前阿斯特拉终于解雇了她。现在她正在准备提起诉讼,她发誓:“如果我必须失去我所有的钱,我也会这样做,以向他们证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