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忆之路到恶劣街道 - 彭博社
bloomberg
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是游乐场。36年前,当我在纽瓦克的总理大道小学上学时,铺砌的后院似乎充满了兴奋的孩子们。至少在记忆中,阳光明媚,老师和孩子们都很快乐。我们这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互相追逐,观看附近绿球场上的大孩子们,忙着将五颜六色的塑料绳编织成珍贵的钥匙链和口哨架。
现在,这个场地常常是空的。在午餐时间,总理的孩子们会在这里短暂玩耍,尽管大门是锁着的,以防他们走失或与附近徘徊的毒贩混在一起。老师和管理员在上下班时都要小心翼翼。游乐场上留下了丑陋的圆形滑痕,显示出汽车盗贼在这里“打转”,闯入场地进行快速旋转的欢乐驾驶。而且没有人有时间去做如此无辜的编织塑料绳的事情。
我曾经称之为家的威夸希克社区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角落里的中餐馆,我在这里学会了爱上用色彩斑斓的瓷杯喝苦茶,现在变成了新信仰福音教会。米特尔曼的面包店,我8岁时独自走去买温暖、刚切好的种子黑麦面包,现在是一家破旧的比萨店。而且再也找不到一个温馨的小餐馆,几枚硬币就能换来一杯蛋奶酒,这是一种既没有蛋也没有奶的苏打水混合饮料,对一个爱吃巧克力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天堂的味道。
为了感受我的家乡发生了多少变化,我在曾经构成我世界的几个街区花了一些时间。我的大家庭在这里生活过,直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才陆续搬到郊区。我的家族是白人迁移的一部分,导致纽瓦克成为城市衰退的象征。然而,回去时,我希望能找到一个与我曾经熟悉的阳光世界没有太大不同的地方。毕竟,威夸希克地区是现任市长夏普·詹姆斯的家乡。这里的种族构成发生了变化,黑人取代了犹太人、德国人和爱尔兰人。但我以为我会发现一个中产阶级社区,房主们维护着他们的财产,并激励他们的孩子过上更舒适的生活。
“这太糟糕了。”我发现了一个战争区域。房主们在那儿,毫无疑问,他们确实自豪地维护着大部分房屋。事实上,我家房子的状况在三十年的磨损下只显得稍微差一点。但在街区的另一边,阴郁的青少年向过路的司机兜售毒品,默默地用一种新的城市信号方式做着手势。破碎的玻璃点缀在靠近路边的草地上,窃贼们砸碎了汽车窗户,盗走了收音机或汽车本身。5月6日,消防员在曾经宁静的威夸基公园发现了两具被谋杀后焚烧的尸体。校长的工作人员害怕走近或甚至开车经过那些角落的居民,其中一些是前学生。“晚上,我不在红灯前停下,”56岁的学校助理埃夫琳·H·肖特说,她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29年。“他们会偷你的车。这太糟糕了。”
在曾被小说家菲利普·罗斯所赞美的学校里,情况也很糟糕,他是威夸基高中的毕业生。去年,纽瓦克的学校被州政府接管,原因是管理不善和学业失败。
在校长那里,面临压力的管理员和教师们努力让学生们抵御压迫他们的问题。一些教职员工本身就是自我奋斗的例子。校长吉纳瓦·W·坎贝尔在纽瓦克贫困的中央区长大。“我告诉孩子们,我的母亲是一名家庭工人。她打扫房子,”坎贝尔说,她深知榜样的力量有多大。
就像现在生活在中产阶级威夸基的孩子们一样,我来自工人阶级背景。我的父亲从未获得高中文凭,他在第一家Pathmark超市之一工作,位于莱昂斯大道,与连锁创始人的儿子们并肩劳动。Pathmark是一家繁忙、不断扩展的企业,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提供了许多晋升机会。在1967年骚乱后不久,Pathmark出售了莱昂斯大道的商店,这对社区来说是一个打击。
我们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搬走了。我的父亲担心如果不把我们带到郊区,我们会和一群坏孩子混在一起。所以我离开了总理学校,去上安全且设施齐全的郊区学校,那里以大学为目标。我的家人非常重视教育。我是七个孩子中的一个,其中五个完成了大学学业。凭借奖学金,我进入了罗格斯州立大学,然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
现在占据那些高天花板旧教室的孩子们面临的挑战比我当初遇到的任何事情都要大。尽管学校保持得很干净,但在外面的街道上,八年级的学生早上曾遭到持枪抢劫。坎贝尔校长说,她的学生中有多达五分之一的人遭受着胎儿酒精综合症、情感或学习困难以及混乱的家庭生活等问题。坎贝尔指出,在她的375名学生中,有些人无法静坐,无法集中注意力。
当然,许多总理学校的年轻人渴望更好的生活。“我的生活将会完美,”六年级学生卡特里亚·C·阿奇在一篇她的老师自豪地张贴在走廊上的作文中写道。“当我成为一名律师时,我将知道该怎么做……我将成为一名最高法院法官……兼职我将成为一名模特……[我]将帮助无家可归者。”一位同班同学写道,她计划成为一名医生或发型师,开一辆雷克萨斯,为她的家人买一栋大房子。
这些孩子实现他们崇高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只能想象。总理大道的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起初的得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到八年级时,阅读成绩下降到全国中位数的25%以下,数学成绩下降到近17%以下。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必须远离街道的诱惑,尤其是来自毒品的轻松钱。八年级教师阿尔方斯·巴斯克维尔回忆起几年前有一位学生来访,谈论他在巴尔的摩成功的包裹递送业务,但他记不起其他成功故事了。
阴暗的未来和我老邻居的威胁日常现实是一个独特的美国种族隔离的遗产。当然,这种隔离并非强制,但在这些街道上的悲剧性与任何法律上的分离一样。假如几英里外的种族骚乱没有导致26人死亡,Weequahic今天会是多么不同?如果像我这样的白人家庭没有逃离,而是接受了那些新来者,他们的愿望无疑与我们自己的愿望没有什么不同,那会怎样?几乎可以肯定,吉恩娜·坎贝尔不会指着学校那几台过时的电脑问我是否有多余的。“我希望能拥有郊区学校的设备,每个教室四五台电脑,”她说。“我的孩子们无法接触到这些。”
从走廊上张贴的作业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另一个几乎无法弥合的鸿沟。作为一种增强自豪感的练习,四年级学生给马丁·路德·金写了信。对外人来说,这个信息令人震惊。“亲爱的父亲,我为你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你帮助了非裔美国人和我们的家庭,”一个女孩写道。“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时,我起初很害怕,因为白人们在扔垃圾桶、水和其他东西。”一位同学补充道:“我不喜欢白人打黑人。我们不会这样对待白人……我不希望黑人被打或被吐口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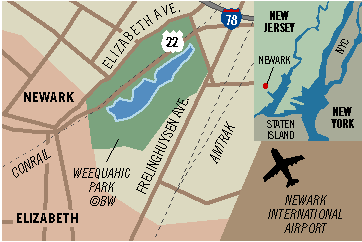
 1960年代的明显种族冲突现在已经很少见,但Weequahic的居民似乎并没有更好。很少有这些年轻人能够拥有无忧无虑、安全的童年回忆。他们无法在邻里中无所畏惧地走动。而且像我这样的外人更是无法做到。
1960年代的明显种族冲突现在已经很少见,但Weequahic的居民似乎并没有更好。很少有这些年轻人能够拥有无忧无虑、安全的童年回忆。他们无法在邻里中无所畏惧地走动。而且像我这样的外人更是无法做到。
变化的社区是严酷城市现实的一部分。也许三十年半的时间不可避免地在我曾经熟悉的和善社区中留下了深深的皱纹。但对我来说,它已不再是同样的地方:它不再是家了。对于那些可能永远不知道健康社区有多么重要的孩子们来说,这些变化只是令人悲伤。对他们来说,Weequahic的辉煌岁月已成为某个陌生人遥远的记忆,这实在是太残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