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红木树的安静运动 - 彭博社
bloomberg
我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偏远的失落海岸的红木修道院的第一天并不算成功。我在我的小水泥块单人房里很舒适,却在早上5点的冥想和晨祷中睡过头,迟到了20分钟才去吃早餐。还有一个问题是要在完全沉默中用餐。修道院的礼仪是一门我不太可能掌握的艺术:我咀嚼我的燕麦片,勺子碰撞发出响声,每次试图压抑我热情的进食时,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喧闹,碰到椅子,然后把自制果酱洒在光滑的混凝土地板上。即使我是一名天主教徒,我也知道我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修士。
然而,这个由十几个人组成的社区似乎并不在意。母亲米里亚姆在修道院的34年中担任院长,几位姐妹和他们的牧师罗杰神父,1962年从比利时搬到这里,致力于在300英亩的森林和起伏的田野中过一种安静祈祷和沉思的生活,这些土地是捐赠给教会的。在搬迁中,这些特拉皮斯特修女带来了近1000年历史的修道院传统。
一旦来到加利福尼亚,修女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被更古老的事物主导的环境中:高耸于她们小定居点之上的2000年历史的红木。修女们的隐修院建在红木林和一个漂亮的苹果园周围。教堂的祭坛坐落在一个从地板到天花板的窗户前,窗外正好框住一棵红木。自然主义者约翰·缪尔,一个深信宗教的人,肯定会赞同。
但这种隐居的生活方式正受到威胁。近年来,木材公司加快了附近的清伐速度,砍伐树木直至修道院的边界。母亲米里亚姆说,有些日子,链锯的尖叫声和倒下的树木的轰鸣声是无休止的。
因此,这个修道院被迫承担起一种不熟悉的温和抗议角色,以保护其生活方式。“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转向上帝,”米里亚姆修女向我解释道。“上帝不仅是内心的灵魂,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一个需要尊重而不是被剥削的礼物。”
昂首阔步的火鸡。我从洛杉矶出发,走了超过600英里,亲眼见证僧侣们拯救红木森林的安静有效的方法。他们的积极方法更多依赖于劝说和调解,而不是对抗。我发现这里是圣所森林,一个700英亩的古老红木林的拼布,被修道院环绕。过去十年里,这些土地是从土地所有者和木材公司手中购买的。资金来自个人的捐款以及1912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拯救红木联盟”。
但僧侣们和当地的环保人士并没有结束。他们正在争取筹集约500万美元,以增加1300英亩现在计划进行伐木的土地。社区还在重建河岸,以恢复因伐木而遭到破坏的鲑鱼栖息地。
在修道院里,僧侣们正在通过种植树木来治愈早期伐木留下的伤痕。我和88岁的罗杰神父一起走到修道院边缘的一片阴凉的年轻红木林。他拥抱着一棵树,深吸一口气,面露微笑。“这些树,”他用浓重的比利时口音说,“将永远在这里,让人们在树下漫步,享受。”它们的存在是因为罗杰神父。年复一年,他每天都在空闲时间清理厚厚的灌木丛,种植幼苗。姐妹们亲切地称之为罗杰林,那里有数十棵茁壮成长的树木,有些现在已经近30岁。这个林地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快乐。
森林和修道院也是上帝野生生物的家园。在海岸附近,一只巨大的罗斯福麋鹿向我冲来,把我赶离他那40头母鹿和小鹿的后宫。在修道院,一只野火鸡在院子里昂首阔步。一对乌鸦在空中飞过,一位修女骑着自行车前往有机蔬菜园。空气中充满了在苹果 orchard 上飞舞的鸟儿的歌声。僧侣们种植自己大部分的食物,并通过烘焙全麦圣餐饼来满足其他需求,这些饼被他们出售给世界各地的教堂。
为了感受外部世界的压力,我与修道院的一位老邻居交谈。当地建筑公司的老板鲍勃·麦基邀请我乘飞机俯瞰森林。我们在浓厚的早晨雾气中相遇,在一个牛牧场,麦基从一座破旧的谷仓里拉出一架泥泞的塞斯纳飞机。我系好安全带,心里想知道跑道在哪里。我们在牧场上滑行,惊散了一打牛,我得到了答案:我们就在上面。
钱生长的地方。起飞后,麦基通过将飞机倾斜到一侧来指出崎岖地形的重要特征,以便直视下方。丑陋的伐木区在森林上留下伤痕,还有一些裸露的土地,木材公司在这里喷洒了除草剂。
麦基的祖父在19世纪在这里定居,曾负责将木材运送到崎岖的海岸装船,他支持适度的伐木。“一棵树大而古老并不意味着它就不该被砍,”他说。这是当地人普遍持有的观点,他们指出一棵古老的红木树的木材价值可能超过50,000美元。麦基反对清理伐木作业,并希望保留一些树林。
所以麦基支持僧侣们的保护工作,并帮助为圣所森林筹集资金。“姐妹们是好邻居,我们很高兴她们在社区中,”麦基说。
回到地面,我陪同22岁的圣所森林实习生本·莫尔豪斯去看看森林的中心:一棵名为“大红”的巨型2000年树。在回来的路上,当本和我愉快地讨论合法化大麻的利弊时,我们在森林厚重潮湿的树冠下迷路了。“别担心,”他在挣扎了一个小时后说。“在森林中找到方向是体验的一部分。”
体验的另一个部分是遇到大卫,一个穿着像黑帮说唱歌手的阴郁年轻人,他站在一个小屋和一大堆铁罐旁。“你不应该来这里,”他告诫道。“如果我的邻居发现你,你就得躲子弹——你会变成堆肥。”我们闯入了戈夫维尔,这是失落海岸自己的贫民窟,起源于禁酒时代的非法酿酒厂。今天,当地的产品更可能是大麻,但我们没有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去发现。
大型示威。很高兴回到修道院安全的环境中,我大口吃着豆腐面包和扁豆汤,喝着道格拉斯冷杉茶。几乎美味。
那天晚上,在祷告服务中,我在姐妹们默默冥想的20分钟里扭动不安。在读完圣经和唱诗后,她们调暗灯光,格里高利圣咏的声音充满空气。一位姐妹缓缓地在黑暗中进行优雅的“祷告舞”,看起来像现代芭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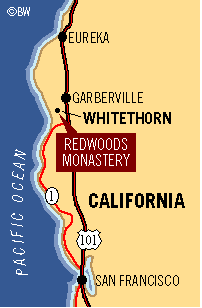 在星期天早晨,这些稀疏人口的山丘中的邻居们来到修道院参加弥撒。许多人是曾经的嬉皮士,他们在1960年代搬到这里,回归土地,逃避动荡的反战运动。一代人后,他们似乎变得温和而安定。在仪式结束时,一位僧侣为那些肆意砍伐树木的人祈求宽恕。然后,几户人家前往北方60英里处的一场大型反伐木示威。出于好奇,我告别并跟随他们。
在星期天早晨,这些稀疏人口的山丘中的邻居们来到修道院参加弥撒。许多人是曾经的嬉皮士,他们在1960年代搬到这里,回归土地,逃避动荡的反战运动。一代人后,他们似乎变得温和而安定。在仪式结束时,一位僧侣为那些肆意砍伐树木的人祈求宽恕。然后,几户人家前往北方60英里处的一场大型反伐木示威。出于好奇,我告别并跟随他们。
这场示威让人隐约想起越南抗议:数百名身穿扎染T恤、褪色牛仔裤和比肯斯托克鞋的示威者大声抗议并被逮捕。我不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我问自己,他们的努力是否能像罗杰神父和红木修道院的僧侣们那样有所成就。也许最终,正是小小的善举和低声的呼唤带来了最大的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