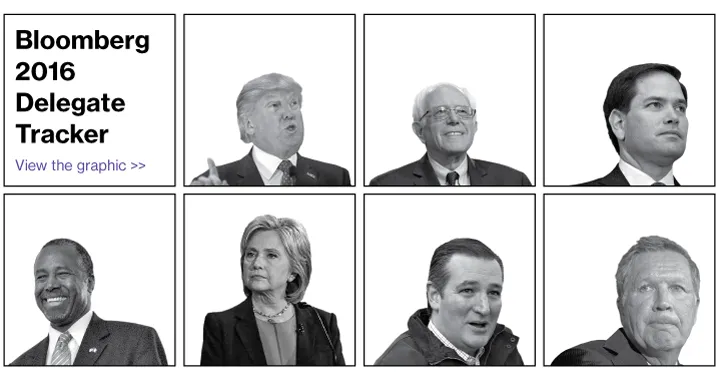伯尼·桑德斯革命背后的精心构建的草根网络 - 彭博社
bloomberg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2月20日内华达州亨德森的党团观察派对上发言。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2月20日内华达州亨德森的党团观察派对上发言。
摄影师:乔·雷德尔/盖蒂图片社在2003年末,扎克·埃克斯利每个月的一个晚上骑上他的自行车,在华盛顿带领自己进行一次游览,参观霍华德·迪恩的支持者在社交网站Meetup上组织的六个聚会。全国范围内有超过800个这样的聚会,许多聚会在酒吧和咖啡馆中,这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第一次在线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系统性地再现。整个秋季,这些聚会是迪恩成功的象征,在许多方面是另一位来自佛蒙特州的政治家今天从左翼挑战民主党建制派的先驱。但即使在迪恩因互联网催生的受欢迎程度不断增长时,埃克斯利也看到了前方的麻烦,显示出不可避免的向混乱转变的迹象。“这就是我所称的烦人的暴政,”埃克斯利说,他现在是伯尼·桑德斯的高级顾问。“最糟糕的人,手头有最多时间的人会接管。”
当时,埃克斯利对互联网行动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了解得和世界上任何人一样多。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是对乔治·W·布什的在线反对派的事实上的领导者。1999年,他购买了域名gwbush.com,并建立了通常被称为第一个政治恶搞网站,里面有经过处理的图片,显示当时的共和党领跑者是一个可卡因用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此事,布什称埃克斯利为“垃圾人”,并沉思“自由应该有界限。”)几年后,作为MoveOn.org的组织主任,埃克斯利帮助指导该组织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应,推动支持者签署可以提交给国会的网络请愿书。在MoveOn的会员基础在在线初选中投票支持迪恩后,埃克斯利被派往他的伯灵顿总部,与对互联网潜在用途感到着迷的竞选领导层分享专业知识和一些MoveOn的工具,以培养支持者。
迪恩是第一个迅速在线筹集大量资金的候选人,他的团队发现,许多捐款者也在帮助组织当地的支持者聚会。但软件缺乏让地方团体指定单一领导者的功能,竞选活动在以其名义进行的聚会中没有官方角色。“你会有10个人报名成为领导者,然后就会发生争论,”埃克斯利回忆道。
最终,迪恩的“人民驱动”运动在最需要强大的时候崩溃了。在他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表现失望之后,这一创新的互联网筹款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可展示的,除了对创新本身的庆祝。在某个时刻,出于一种理想化的尝试,试图让聚会朝着生产力的方向发展,竞选活动曾要求与会者给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发送手写信。“实际上写的信件数量微乎其微,根本无法追踪,”埃克斯利回忆道。“迪恩的竞选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潜力。”
 扎克·埃克斯利(右)和贝基·邦德,伯尼2016总统竞选的高级顾问,2016年2月19日在拉斯维加斯。
扎克·埃克斯利(右)和贝基·邦德,伯尼2016总统竞选的高级顾问,2016年2月19日在拉斯维加斯。
摄影师:大卫·保罗·莫里斯/彭博社埃克斯利前几天与贝基·邦德在参观桑德斯竞选的内华达州总部后,回忆起那些痛苦的经历,邦德也是该竞选的高级顾问。埃克斯利和邦德在2000年首次见面,当时她拨打了他出现在的NPR节目。埃克斯利正在谈论他的闪电行动项目,要求佛罗里达官员计算每一票在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中;邦德刚刚发起了一项在线请愿,要求国务卿凯瑟琳·哈里斯也这样做。对于这两位46岁的人来说,近年来在线行动主义的历史是一条错失机会的时间线,群众运动在任何政治专业人士能够弄清楚如何将有机能量转化为战术收益之前就已经消失。自去年秋天联手以来,这两位朋友一直在努力设计一个能够承载和支持桑德斯运动的框架,并引导其走向民主党提名的道路。“因为扎克以前见过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当媒体开始报道[桑德斯],人们发现他是可行的时候,会有一股巨大的热潮,”邦德说。
本月早些时候,热潮来临。桑德斯实现了迪恩从未做到的事情:他在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中仅差一个百分点就赢得了胜利,并在新罕布什尔州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数百万美元以小额捐款的形式涌入,热情的支持者们纷纷注册到他的网站上。这一次,竞选活动有真实的任务可以立即交给他们,而不需要相应规模的工作人员来管理。“你可以借鉴迪恩的经验,以及小额筹款可以提供这种合法性和可行性的想法,”邦德说。“我们已经用桑德斯的小额筹款复制了这一点,但我们还增加了另一个元素,那就是实际上让所有对桑德斯充满热情的人,不仅仅是给他们机会捐款,还给他们机会参与一些选举工作。”
桑德斯所有利用他在前四个初选和党团会议州的成功来在其他地方竞争的计划,都依赖于埃克斯利和邦德迅速扩大一个在他们未曾预料到候选人会有与希拉里·克林顿一样多资金的阶段构想的机制——而这将在他有资金但时间紧迫的时刻受到考验。邦德称之为“大型组织”,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志愿者机构,由一系列看似微小的技术创新所实现,埃克斯利希望这能实现不仅是迪恩竞选的未竟梦想,还有占领华尔街、塔赫里尔广场和弗格森的梦想。“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模型的局限性,这个模型认为如果你能让很多人做某事——你只需涌上街头,”埃克斯利说。“如果没有真正建立一个能够提供领导力的组织,那么在推翻穆巴拉克之后你能得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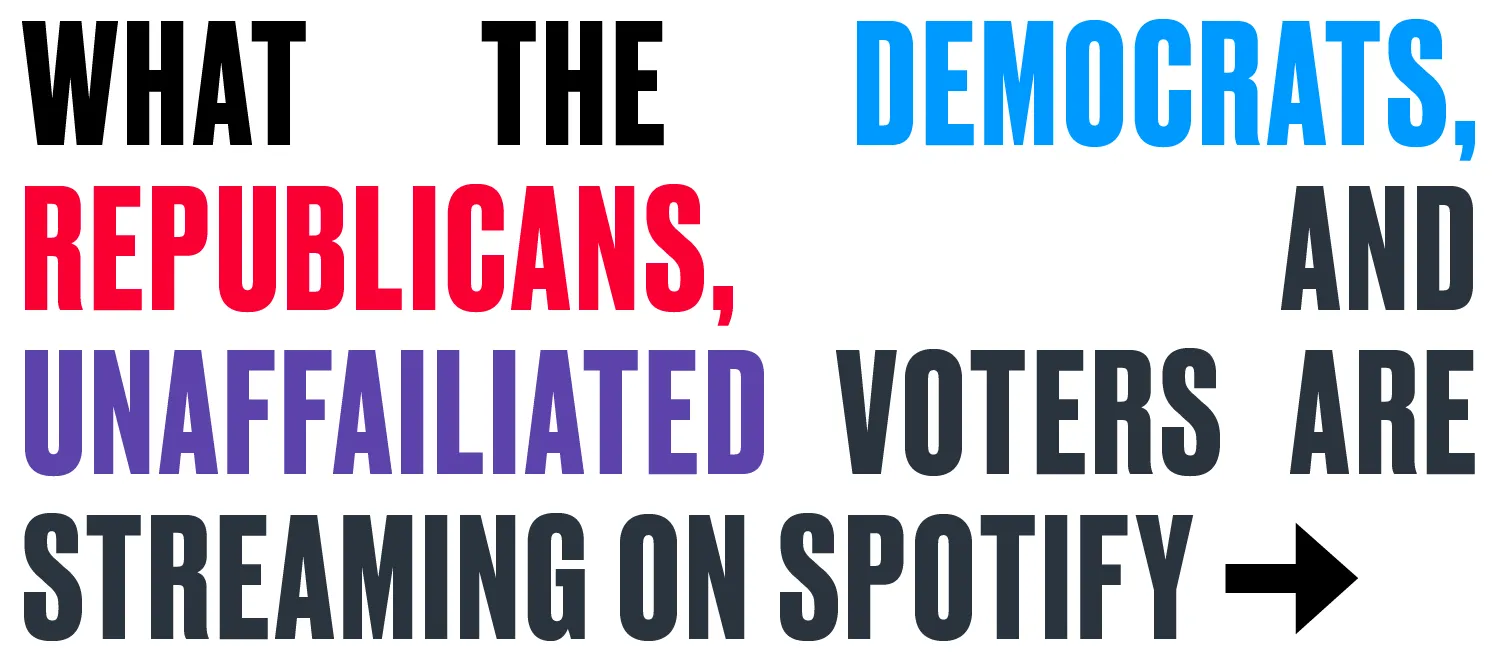 **桑德斯集会上的庞大人群是媒体报道他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揭示性的出席人数可能是近50,000名桑德斯支持者,他们在全国各地参加会议,却没有看到候选人。“‘感受伯恩’纳什维尔集会将不包括伯尼·桑德斯,”一篇稍显困惑的 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在其中一次集会前报道。这就是在线组织展现其持久效力的地方。
**桑德斯集会上的庞大人群是媒体报道他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揭示性的出席人数可能是近50,000名桑德斯支持者,他们在全国各地参加会议,却没有看到候选人。“‘感受伯恩’纳什维尔集会将不包括伯尼·桑德斯,”一篇稍显困惑的 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在其中一次集会前报道。这就是在线组织展现其持久效力的地方。
在超过两百次的场合中,桑德斯的竞选团队要求当地支持者确保一个场地——一个工会大厅或教堂,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的一个公共房间,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朗·钱尼剧院——并向所有在其档案中有电子邮件地址的30英里半径内的人发送邀请,邀请他们参加一个“官方组织会议”,会议上没有他们听说过的任何人。凭借如此微薄的诱饵,竞选活动吸引了450人到西雅图,470人到路易斯维尔。“使用电子邮件列表的美妙之处,”埃克斯利说,“在于它能吸引大量新的人。绝大多数与会者总是那些从未参与过竞选活动的人——通常也从未参与过任何竞选活动。”
埃克斯利和邦德希望在一个小时后将他们送回世界,不仅作为志愿者,还作为初步的领导者。这种政治洗礼的概念与整个进步神学相悖,这种神学可以追溯到索尔·阿林斯基的影响力著作,认为活动家必须经过缓慢、渐进的觉醒。“这种组织方式变得如此乏味,”埃克斯利说。“组织者开始产生这样的期望:组织应该是极其困难的。”
在2004年大选后,他担任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线传播和组织的主任,埃克斯利决定离开选举政治。次年,他共同创办了新组织学院,该学院直到十年后解散的那一年,一直作为左翼活动家的重要培训和研究机构,并逐渐远离政治职业,最终定居在他妻子位于密苏里州西南部的家乡。“他没有成为政治顾问,没有搬到华盛顿特区,也没有建立一家公司,这一点相当显著。他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2004年担任院长网站管理员的尼科·梅尔(Nicco Mele)说。“扎克成功地创造了这个领域,而从未与基层和业余活动者保持距离。”
埃克斯利通过迪恩(Dean)老兵的散居与总统政治保持联系,深化了他对政治组织的理解。在2007年底,埃克斯利前往拉斯维加斯,与其中一位老兵罗比·穆克(Robby Mook)见面,穆克已成为克林顿在内华达州的党团竞选主任——而他恰好是克林顿目前的经理。穆克邀请埃克斯利观察他的工作。穆克的运作与埃克斯利在四年前的竞选中看到的截然不同,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并专注于对可衡量结果的持续跟踪。“如果我培训某人,并让他们对在一个选区内实现整体目标负责,他们会比我只是说,‘去找三个支持者,然后再回来找我,’要努力得多,”穆克对埃克斯利说。
埃克斯利在前往俄亥俄州见杰里米·伯德时,看到了一种不同的现代竞选观。伯德曾与穆克一起在迪恩的新罕布什尔州团队工作,随后负责巴拉克·奥巴马在这个关键州的普选活动。埃克斯利对奥巴马的做法印象更深刻,部分原因是他更注重赋予志愿者在社区中领导结构化团队的能力。“我们在时间表上做出了决定,”伯德告诉埃克斯利,组织者“不会根据他们在夏季进行的选民接触数量来衡量——而是根据他们招募、培训和测试的志愿者数量。”伯德在两次总统竞选中帮助塑造了奥巴马的全国性现场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社区团队模型。“这些组织温床——尤其是在民主党方面——正在培养出一代新的活动家,他们既有纪律又有技能,同时也充满热情,”埃克斯利在《赫芬顿邮报》发布的旅行报告中惊叹道。“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组织工作是在一个工会,要求的日常问责水平与穆克的竞选活动相似。但我导师主要的执行手段是传统的老左派手段:恐惧。他常常对我们大喊大叫或用恶毒的语言侮辱我们,当我们未能完全按照指示完成任务时。实际上,这对我来说效果很好。但这一代新的左翼领导者更倾向于信任和尊重。”
奥巴马团队渴望将竞选活动中常常被顾问视为繁琐工作的部分专业化,使得工作人员组织者在现场竞选中变得更加核心。全职的有薪员工是必要的,因为他们促进了招募、培训和激励志愿者的许多后勤工作,志愿者在所谓的参与阶梯上逐步上升,并管理可以聚集在一起的办公室。“他们所建立的真的很美好,但这一切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美国人民需要被唤醒意识,才能参与其中,”埃克斯利谈到奥巴马结构时说道。“志愿者被整合到一个组织中,他们在一个团队里,拥有角色和责任,但每一个人都离工作人员只有一步之遥。”
埃克斯利认为,对专职员工的关注反映了对“堆石模式组织”的过度尊重,仿佛任务的艰巨和重复性确认了目标的美德。没有人比奥巴马本人更能体现这种殉道精神,他曾写到他在芝加哥南区作为社区组织者时所学到的“共同牺牲”。“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左派的框架是我们必须说服人们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埃克斯利说。“在他们的许多斗争中,他们感到自己是与美国人民对立的,这成为了他们的心态。”
当埃克斯利在七月加入桑德斯的竞选时,建立一个类似于奥巴马的、需要大量工作人员的基层组织——而当时穆克和伯德正在为克林顿组建的那种——甚至都不是一个选项。伯灵顿的竞选领导层已经制定了被描述为“传统竞选”的计划,尽可能多地在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配备地面工作人员。其余国家被指定为“非工作人员”州。发生在这些州的任何事情都必须由志愿者自己来培养;很可能在桑德斯在早期州赢得胜利之前,竞选领导层无法将官方资源转移到后来的州。第一轮党团会议和3月1日超级星期二之间的日历恰好有一个月,因此在爱荷华州投票之前,支持桑德斯竞选的任何人力基础设施都必须到位。“在奥巴马身上确实有势头,但增长只来自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以与人们互动,”埃克斯利说。
在54个非工作人员州和地区,支持者在整个夏季都只能靠自己。当科尔宾·特伦特成立田纳西州支持伯尼·桑德斯时,他自然而然地开始在他位于莫里斯敦的家附近组织聚会。参与者能够开始收集签名,以使桑德斯有资格参加该州3月1日的选票,并注册新选民。但一旦完成这项工作,田纳西州的人们就没有太多其他事情可以做来推动竞选的战术目标。
到秋天,特伦特——一位烹饪学院毕业生,他将出售自己的“疯狂好汉堡”食品车,以便全心投入竞选——已经 团结了几个独立出现的不同团体,以帮助桑德斯在全州范围内。埃克斯利深知这些支持者因现代组织理念而有效地被孤立的悲惨历史,因此计划前往田纳西州与他们直接接触。他和特伦特安排了一个五个城市的行程,称之为“现场组织会议,” 向每个附有田纳西地址的竞选电子邮件名单上的名字发送了一次通知。
埃克斯利认为,眼前这些小而积极的群众嘲弄了组织者的信条,即将公民“向上推进参与的阶梯,最终当你完成他们时,你已经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完全形成的政治人,现在他们准备组建一个社区团队,”正如埃克斯利所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在那里。他们已经是自己教堂、犹太教堂、社区组织、乐队、家庭和工作场所的领导者。他们已经愿意为桑德斯的胜利做任何事情。”
现在,竞选所要做的就是弄清楚如何让这样的田纳西人对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赢得选票有用——如何将桑德斯的全国能量像激光一样集中在他需要胜利的地方。
 扎克·埃克斯利(Zack Exley),右侧,和贝基·邦德(Becky Bond),2016年伯尼总统竞选的高级顾问,2016年2月19日在拉斯维加斯的比特咖啡馆和唱片店外拍照。
扎克·埃克斯利(Zack Exley),右侧,和贝基·邦德(Becky Bond),2016年伯尼总统竞选的高级顾问,2016年2月19日在拉斯维加斯的比特咖啡馆和唱片店外拍照。
摄影师:大卫·保罗·莫里斯(David Paul Morris)/彭博社埃克斯利理论上驻扎在桑德斯位于佛蒙特州的总部,但在整个秋冬季节他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他所称的“巡回演讲之旅”上,复制他和特伦特所开创的通过复兴会议召集新志愿者的模式。埃克斯利坚持认为,他正在开发的将他们联系起来的团队——他称之为“分布式组织”,利用技术将遥远的劳动力源连接起来——即使他们的主要工具是互联网,也不应被归类为数字工作人员。“在某个时刻,组织者开始使用电话,但我们没有电话组织部门,”邦德说。
邦德的职业生涯一直处于激进主义和电话业务的交汇点。当她在2000年第一次遇到埃克斯利时,她在工作资产长途电话公司(Working Assets Long Distance)工作,这是一家通过信用卡和电话服务提供商,将利润用于进步派小组。为了成为桑德斯的全职顾问,邦德从她在公司(现已更名为CREDO Mobile)担任副总裁的职位上请假,在那里她帮助发起了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其第一个项目是击败与茶党相关的国会议员。
当邦德在九月份加入竞选时,很明显任何长途电话拨打操作都将受到技术限制的阻碍。埃克斯利在2004年帮助启动了 JohnKerry.com 呼叫中心,尽管自那时以来进行了显著的改进——通过将电话功能直接集成到网络界面中——但从家中拨打电话仍然远不如从现场办公室高效。在那里,电话银行的志愿者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预测拨号器,这些拨号器——预见到人类接听电话的几率很低——使用算法同时拨打多个号码,然后将一个实时呼叫者连接到有人接听的线路上。然而,在桑德斯邀请非工作人员州志愿者使用的平台OpenVPB上,呼叫者必须通过网站手动召唤每个电话号码,这是一种缓慢且令人沮丧的过程,埃克斯利担心这会让他们感到气馁。
在一个其最深层支持来自不太可能拥有固定电话的年轻选民的竞选中,更令人担忧的是,无法使用预测拨号器拨打手机。正如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在一项声明性判决中确认的那样,1991年的《电话消费者保护法》要求所有拨打手机的电话必须由实时呼叫者手动发起。(该法律的 相关条款 是许多民调机构发现拨打代表性手机样本的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在12月,邦德最终指导志愿者程序员找到了一种他们称之为“伯尼拨号器”的临时解决方案。该竞选与一对商业可用的预测拨号系统签订了合同,然后开发了一个程序,自动按目的地对电话目标进行排序:固定电话被路由到预测拨号器,而手机号码则被分派给一组志愿者,他们手动排队以满足联邦法规。这种协调现在对呼叫者来说是不可见的,他们通过网络平台登录,并在脚本的指导下,个人电话依次连接到手机和地面号码进行调查。“他们每小时与三到四个人交谈,而是与20个人交谈,”邦德说。
在全国范围内,Exley 和 Bond 解释了让志愿者承担这项工作的逻辑,以及在公共场合而不是单独打电话的价值。“谁,”他们在他们称之为 barnstorm 的会议上已经问了几十次,“想成为电话银行的英雄?”在举手后,一位组织者将志愿者带到一旁,并给他们一个日历,指示他们圈出愿意将家里变成电话银行的日期。然后,新任命的电话银行主持人回到大组中,向大家推介他们的活动,邀请与会者在活动结束后立即上前报名参加他们想参加的活动。“我们不让他们回家,获取他们的电话号码再打给他们,”Bond 说。“突然间,你就有了这些承诺参加某个日期的人,还有这些即将到来的人——而且他们已经见过即将到来的人。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在发生。”
2月7日,在爱荷华州与希拉里·克林顿几乎平局的六天后,Pete D’Alessandro 带着他的部分现场工作人员从德莫因出发,沿着35号州际公路向南行驶。D’Alessandro 可能可以选择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任务。然而,正如他告诉人们的那样,他渴望去俄克拉荷马州——十年前他为一位民主党国会候选人工作过的地方——因为这将带来一个与他在四月同意担任爱荷华州竞选协调员时所面临的挑战相似的挑战。“我并不是为了轻松的机会而做这个,”他说。
在可以说是美国最保守的州中,赢得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初选可能并不像听起来那么不切实际。除了可能被自由派活动家占据的两个党团会议(明尼苏达州和科罗拉多州)和两个新英格兰初选(佛蒙特州和马萨诸塞州)之外,俄克拉荷马州——拥有白人农村人口和历史悠久的草原民粹主义——可能代表了桑德斯在3月1日获得直接胜利的最佳机会。当 D’Alessandro 请求带一些他在爱荷华州的顶尖工作人员来建立桑德斯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首次官方存在时,一位名叫 Zach Fang 的现场组织者位于他的名单之首。
方在桑德斯团队中让自己声名鹊起,成为说服竞选领导层相信电话可能已经是与选民联系的过时工具的人。在2014年的一次竞选中,方注意到被分配打电话的年轻志愿者们偷偷地给他们的联系人发送短信,而不是按照指示拨打电话。“是刚大学毕业的孩子们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像是做错了事一样向他们的上司——现场组织者——隐瞒这一点,”25岁的方说。当他最终自己尝试时,他明白了原因;那些永远不会接听陌生号码来电的人可能会注意到来自某个号码的短信。“我们为什么不以人们彼此沟通的方式与他们沟通呢?”方说。“他们不想打电话。他们想要收到短信。”
方发现了Hustle,这是一款由旧金山初创公司开发的应用程序,允许组织者从自己的手机上集中跟踪发送的短信。从2008年开始,竞选活动开始积极收集手机号码,以便能够给支持者发送短信,但当他们这样做时,通常是发出一条没有个人色彩的消息,附带行动号召:投票提醒或捐款请求。这些消息并没有邀请回应,任何回复的人通常会收到自动回复,如果有的话。方意识到,通过Hustle,组织者可以通过发送邀请回答的问题来发起实际的短信对话,然后与这些回复进行个别互动。(该应用程序会隐藏收件人的号码,记录所有交流,以便作为持续互动的一部分进行文档记录。)起初,方尝试使用该程序通过询问他们支持谁来识别选民——“人们会问,‘你为什么给我发短信?’”——但当他向已知支持者发送邀请他们参与的消息时,发现成功率大大提高。“这不是关于大规模发送信息,这就是我们过去对数字的看法,”方说。“这关乎与人们建立关系。你可以更快地做到这一点。”
方和达莱桑德罗发展了一种跨代的奇特组合动态,这位25岁的组织者嘲笑他52岁的老板通过将候选人的日程安排贴在办公室墙上而不是在屏幕上来跟踪日程。“我就是这么老派,”达莱桑德罗说。但当组织者们在8月底为州党举办的杰斐逊-杰克逊晚宴努力聚集人群时,他变得信服;他们在16小时内成功吸引了235名参与者,而60名工作人员花费了2200小时才获得首批465个承诺。“我想我在自己生活中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与朋友通过短信进行多少对话,”达莱桑德罗说。
在2月8日开始在俄克拉荷马州工作时,他发现了一小群热心的支持者,但他们的热情却没有带来多少选举工作。桑德斯的志愿者们主动联系,进行了最少的选民接触:他们在塔尔萨敲了不到1000扇门。达莱桑德罗安排埃克斯利来到该州进行宣传会议,方开始使用Hustle联系州内已知的支持者邀请他们。在48小时内,他安排了321名参与者。埃克斯利在俄克拉荷马城的宣传活动吸引了381名参与者;在塔尔萨,有313名参与者。(根据方的说法,该州58%的目标选民集中在这两个城市。)在接下来的周末,包括总统日假期,218名志愿者在全州范围内接触了8000扇门。
使用Hustle使桑德斯在俄克拉荷马的小型团队能够迅速挑选出活跃的志愿者,在那些民主党选民稀少到没有任何竞选活动会考虑开设现场办公室并安排全职组织者的地区。“很多竞选活动会完全忽视这些人口为3000或5000的小镇,那里有六个可步行的区域,”方说,他提到埃尔克城和塔赫基瓦,然后以韦诺卡为案例研究,这里人口927,距离下一个人口中心很远。“一个人,”他说,“每个周末都能敲响那个小镇的每一扇门。”
当埃克斯利在内华达州到达时,距离党团会议还有一周,桑德斯和克林顿的竞选活动 都已经转向了动员投票工作。对于克林顿来说,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10个月过程的最后阶段 派驻基层组织者 以便与支持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些支持者将成为志愿者,然后自己在他们的社区中识别支持者以进行动员。桑德斯在该州的存在时间只有一半,而埃克斯利和邦德在其中大部分时间里工作,以便让基层工作人员完全跳过早期的许多工作。当伯尼拨号器在12月启动时,是外州的志愿者在努力识别内华达州民主党人的偏好,以便当地的组织者和志愿者可以直接转向与他们希望 动员的对象进行更实质性的接触。“我们知道,黄金标准是面对面、邻里之间的沟通,因此如果我们能腾出他们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将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上面——通过识别那些他们不需要交谈的人,那些与我们站在一起并需要被动员的人——这就解决了大部分的基层计划,且只需小型团队和技术,”她说。
当内华达州人周六去参加党团会议时,邦德重新调整了伯尼拨号器。许多电话仍在拨打南卡罗来纳州,那里的初选将在周六举行,但多余的能力被转移到识别3月1日州如田纳西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桑德斯支持者,为特伦特和方等人招募的志愿者创造目标。邦德表示,已有50万桑德斯支持者报名成为志愿者,约有一千人每天拨打电话——总共拨打了100万次。“我们可能已经发展出历史上最大的选民联系能力,”桑德斯的数字总监肯尼斯·彭宁顿说。“在这个开始阶段,我们有这个巨大的机器,但我们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他们找到了使用这个机器的方法。”
没有什么能像他看到新志愿者迅速转变为职员那样验证埃克斯利对员工组织的怀疑。上周的一个下午,他进入了一个Slack频道,帮助台的志愿者们在这里交流建议,他对自己无法跟上他们使用的官方术语感到惊讶。“我想知道‘PC’代表什么,”埃克斯利说。“他们想出了所有这些缩略词!”
埃克斯利和邦德坐在一家咖啡馆的人行道野餐桌上,打开笔记本电脑以监控呼叫量和团队通过Slack频道私下交流的不断增加的数量。他们距离在线供应商 Zappos 的总部仅有三个街区,而正是这家公司——以其著名的客户服务和对 消除老板 的新承诺——成为了他们所建立的更好的模型,而不是奥巴马的任何竞选活动。“这真是一个现代化的虚拟呼叫中心,”埃克斯利说。
他与邦德的对话经常飘向一种幻想,想象如果有时间继续扩展,这将是什么样子,志愿者们在没有员工直接干预的情况下招募和培训其他志愿者。“这是一个有机运动,但我们可以发展它,”她说,拥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在全国范围内充当完全合格的员工。”埃克斯利甚至创造了一个术语,“后稀缺组织”,来描述一种普选场景,在这种场景中“我们可以敲响全国每一扇门,拨打每一位选民的电话。”
他现在有志愿者在培训其他志愿者,在他尚未到达的国家部分进行宣传。“他们将会培养大量的电话银行志愿者,增加我们的能力,然后我们将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接触到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如果我们能在超级星期二之前活下来,这一切只会不断增长,”埃克斯利说。
“最大的悲剧将是如果这一切来得稍微有点晚,”他补充道,停顿了一下,罕见地表现出宿命论。“这总是这样,在所有这些竞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