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地区的朝圣者 - 彭博社》
bloomberg
 国会图书馆,地理与地图部/马克·伯恩斯/城市实验室我为在芝加哥的一周轻装上阵,完全打算带着同样轻便的随身行李回到拉瓜迪亚。但我却不得不在两个时区的两个公共交通系统中挣扎,背着一个鼓胀的背包和一个明显更重的行李箱,甚至得坐上去才能关上。我还得同时 juggle 一个笨重的纸板海报管和一个装在拉链不太好使的软袋里的音乐会尺寸的共鸣乌克丽丽。
国会图书馆,地理与地图部/马克·伯恩斯/城市实验室我为在芝加哥的一周轻装上阵,完全打算带着同样轻便的随身行李回到拉瓜迪亚。但我却不得不在两个时区的两个公共交通系统中挣扎,背着一个鼓胀的背包和一个明显更重的行李箱,甚至得坐上去才能关上。我还得同时 juggle 一个笨重的纸板海报管和一个装在拉链不太好使的软袋里的音乐会尺寸的共鸣乌克丽丽。
我在芝加哥生活了大约12年,从大学迎新到2014年秋季,当时我为了工作搬到了布鲁克林。从我在阿巴拉契亚俄亥俄州的家乡来到芝加哥,我担心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再也听不到安静。我担心我会讨厌它的平坦。相反,我发现冬天让我有了 bragging rights,而为了夏天的荣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学会了如何找到我的人和我的去处。我学会了我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其中一部分就是学会何时尝试新事物。
彭博社城市实验室对于租户来说,人工智能驱动的筛选可能成为住房的新障碍高盛测试家具销售商Wayfair的债务需求新泽西-纽约市通勤者在最新的交通混乱中被困在公交车和火车上在创纪录的炎热夏季之后,空调强制令的压力加大但我不打算让东海岸改变我:我带着一件“中西部最好”的T恤、来自最喜欢的地方的杯子和心爱的场馆的演出海报来到了我的新公寓。
然后我远离了芝加哥。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无法忍受回到我如此热爱的地方的想法。当我终于装饰我的公寓时,只有一幅小小的商品市场艺术印刷品挂在我的墙上。我想,如果我把太多芝加哥的视觉元素放在眼前,我会后悔离开。
 当然,你的旧家不会那么容易消失。康尼岛很不错,但我想念密歇根湖。我找不到合适的汉堡、合适的啤酒、合适的比萨。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我为我失去的艺术学院会员资格感到悲伤。即使我心爱的即兴莎士比亚公司在曼哈顿演出,他们的演出费用是两倍,时长却只有一半。
当然,你的旧家不会那么容易消失。康尼岛很不错,但我想念密歇根湖。我找不到合适的汉堡、合适的啤酒、合适的比萨。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我为我失去的艺术学院会员资格感到悲伤。即使我心爱的即兴莎士比亚公司在曼哈顿演出,他们的演出费用是两倍,时长却只有一半。
彻底戒掉芝加哥并没有奏效。搬回去也不在计划之中。但我终于在上个月让自己去了一趟。即使是从奥黑尔机场跑道远远看到的西尔斯(是的,西尔斯)大厦也让我泪水夺眶而出。身处我的城市——火车上的广播听起来是那么熟悉,而我常去的中餐馆老板在我走进门时紧紧拥抱我——让我感到无比恢复。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我现在在纽约付房租。我必须在我的一周结束后离开。
解决方案一半是聪明才智,一半是囤积本能。在 超市扫货的伟大传统中,我填满了我的购物车。如果上面有芝加哥的旗帜、芝加哥的社区、市政符号或当地标志,我就买下它。我买了带有红色六角星的激光切割木耳环。我买了带有我旧区号(773!)和棕线站(达门!)的磁铁。我买了一个旗帜补丁,准备缝在我肩包上的布鲁克林工业标签上。我买了宣称“我宁愿在芝加哥!”的徽章。我沮丧地抵制了超大复古地图重印、手工制作的芝加哥旗帜切菜板、WPA风格的旅游陷阱海报。我在我最喜欢的独立书店和漫画店买了太多书,并保留了购物袋、收据和书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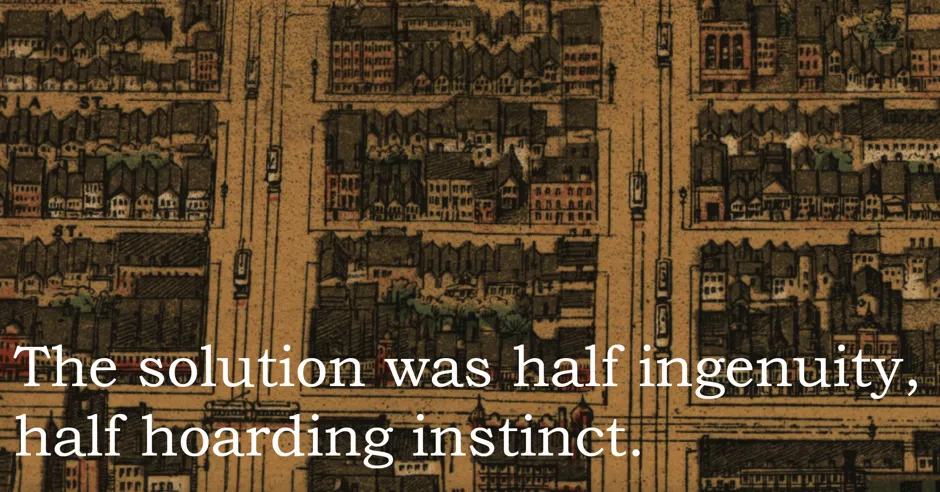 我的芝加哥是一个有限的、特权的和被改造的地方。我知道这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就像它的地方自豪感一样。尽管如此,这似乎是恒定的:芝加哥人喜欢来自芝加哥。他们喜欢在那儿生活,也喜欢离开时的感觉。当我在其他地方佩戴我的星星耳环、Half Acre T恤或精致的黄铜旗帜项链时,我在等待另一个芝加哥人来完成一个秘密握手。你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得到一幅帝国大厦的批量印刷画布。我不知道有哪个纽约人穿纽约的东西。芝加哥有一种广泛采用的视觉语言,但芝加哥人是 解读它的人。居民们认同这种图标。它仍然是我们的。
我的芝加哥是一个有限的、特权的和被改造的地方。我知道这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就像它的地方自豪感一样。尽管如此,这似乎是恒定的:芝加哥人喜欢来自芝加哥。他们喜欢在那儿生活,也喜欢离开时的感觉。当我在其他地方佩戴我的星星耳环、Half Acre T恤或精致的黄铜旗帜项链时,我在等待另一个芝加哥人来完成一个秘密握手。你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得到一幅帝国大厦的批量印刷画布。我不知道有哪个纽约人穿纽约的东西。芝加哥有一种广泛采用的视觉语言,但芝加哥人是 解读它的人。居民们认同这种图标。它仍然是我们的。
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我们更重视体验而不是物品。这正是“我得到的只是这件糟糕的T恤”的全部意义。然而,在我访问的中途,我站在老城民谣音乐学校的一面乐器墙前。我一直在告诉每个人,无论是陌生人还是朋友,关于我自从搬走后第一次回来的事,以及我想再次做所有事情。我想知道一切是否仍然存在。一位员工微笑着给了我一些乙烯基标志贴纸。我无法将目光从这把尤克里里上移开。
它是桃花心木的,比我那把小初学者的高音尤克里里更重、更大。琴身底部有一个美丽的穿孔金属板,带有小提琴般的f孔,颈部镶嵌着闪亮的鲍鱼。它在我手中感觉很好。我买我的第一把尤克里里是因为它能让任何东西, 甚至 哈姆雷特,听起来快乐。这把则讲述了我不同的故事。在芝加哥,有一个我想成为的人,他创作音乐和艺术,跳林迪舞,参加即兴表演团队。等我作为客人回来时,很多这些都已经被抛在了一边。难怪我对回去如此犹豫。
芝加哥开启了我可以成为的样子。你可以向前走,而不必抛弃你所爱的事物。那些东西并不是经历,也不是自我认知。但尤克里里如此便携,这是一件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