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弗罗里达与新的城市危机 - 彭博社
Richard Flori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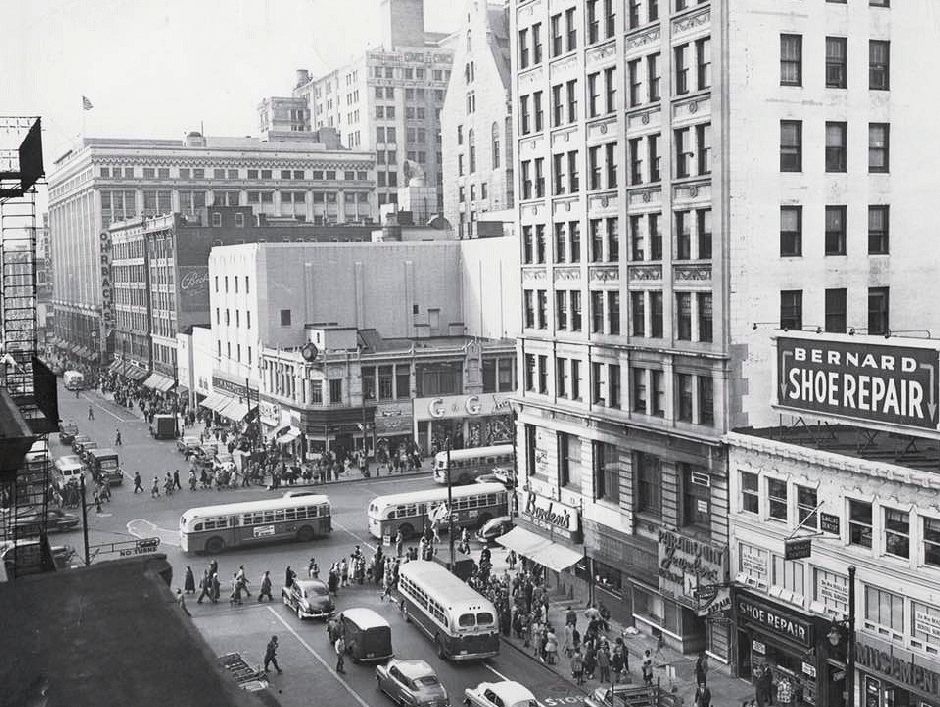 布罗德和市场街,纽瓦克,新泽西州,大约1960年代公共领域/OldNewark.com城市似乎深深印在我的DNA中。我于1957年出生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那时它是一个繁荣的城市,熙熙攘攘,有标志性的百货商店、早晚报纸、图书馆和博物馆、繁忙的市中心以及庞大的中产阶级。我的父母和其他数百万美国人一样,在我还是个幼儿时搬到了郊区。他们选择了距离纽瓦克大约十五分钟车程的小镇北阿灵顿。他们这样做,正如他们常常提醒我的那样,是因为这个小镇提供了良好的学校,特别是他们认为能为我和我兄弟准备大学的天主教学校——和平女王学校,这让我们走上了更好的生活道路。尽管我们已经搬出了纽瓦克,但我们仍然在大多数星期天回到老邻居,和我的祖母及仍然住在那里的一家人一起享用丰盛的意大利晚餐。
布罗德和市场街,纽瓦克,新泽西州,大约1960年代公共领域/OldNewark.com城市似乎深深印在我的DNA中。我于1957年出生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那时它是一个繁荣的城市,熙熙攘攘,有标志性的百货商店、早晚报纸、图书馆和博物馆、繁忙的市中心以及庞大的中产阶级。我的父母和其他数百万美国人一样,在我还是个幼儿时搬到了郊区。他们选择了距离纽瓦克大约十五分钟车程的小镇北阿灵顿。他们这样做,正如他们常常提醒我的那样,是因为这个小镇提供了良好的学校,特别是他们认为能为我和我兄弟准备大学的天主教学校——和平女王学校,这让我们走上了更好的生活道路。尽管我们已经搬出了纽瓦克,但我们仍然在大多数星期天回到老邻居,和我的祖母及仍然住在那里的一家人一起享用丰盛的意大利晚餐。
彭博社城市实验室美国人如何投票导致住房危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转学生提供专门建造的校园住所熊队首席警告芝加哥没有新NFL体育场的风险罗马可能开始对特雷维喷泉收取入场费然后,在1967年一个炎热的七月天,当我九岁时,我看到城市被动荡所吞没。当我的父亲开车带我们进入城市时,空气中弥漫着浓烟:纽瓦克被其臭名昭著的骚乱所吞没,警察、国民警卫队和军用车辆在街道上排成一列。最终,一名警察拦下我们,警告我们有“狙击手”。当我的父亲焦急地掉头时,他指示我趴在地板上以确保安全。
 后果:1968年3月7日,新泽西州纽瓦克的斯普林菲尔德大道,骚乱爆发一年后。约翰·杜里卡/AP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我目睹了后来被称为“城市危机”的展开。中产阶级和工作岗位纷纷逃离像纽瓦克这样的城市,转向郊区,导致城市经济空心化。到我在1970年代初进入高中时,纽瓦克的大部分地区已成为经济衰退、犯罪和暴力上升以及种族集中贫困的受害者。我毕业的那一年,1975年,纽约市濒临破产。不久之后,我父亲的工厂永远关闭,使他和数百人失业。希望、繁荣和美国梦已转移到郊区。
后果:1968年3月7日,新泽西州纽瓦克的斯普林菲尔德大道,骚乱爆发一年后。约翰·杜里卡/AP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我目睹了后来被称为“城市危机”的展开。中产阶级和工作岗位纷纷逃离像纽瓦克这样的城市,转向郊区,导致城市经济空心化。到我在1970年代初进入高中时,纽瓦克的大部分地区已成为经济衰退、犯罪和暴力上升以及种族集中贫困的受害者。我毕业的那一年,1975年,纽约市濒临破产。不久之后,我父亲的工厂永远关闭,使他和数百人失业。希望、繁荣和美国梦已转移到郊区。
当我那个秋天去拉德格斯大学时,我发现自己被关于城市及其种族、贫困、城市衰退和工业衰退问题的课程所吸引。当我大二时,我的城市地理教授罗伯特·莱克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们游览下曼哈顿并记录我们所见。我被正在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变化所吸引,尤其是在索霍、东村及周边地区,被街道和生活在那里的艺术家、音乐家、设计师和作家的活力所迷住。旧工业仓库和工厂正在转变为工作室和居住空间。朋克、新浪潮和说唱音乐正在为该地区的音乐场所和俱乐部注入活力——这正是后来成为全面城市复兴的第一缕嫩芽。
但正是在匹兹堡,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MU)教授了近二十年,我开始理清影响美国城市的主要因素。匹兹堡因去工业化而遭受重创,失去了数十万人和大量高薪工厂工作。根据既定的经济发展智慧,匹兹堡的领导者试图通过提供税收减免和类似的激励措施来吸引公司;他们投入资金建设补贴的工业和办公园区;他们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会议中心和两个闪亮的体育场。
 从杜肯山俯瞰匹兹堡Dllu/Wikimedia Commons由于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医疗中心和企业研发单位,以及主要的慈善机构,这座城市能够抵御最糟糕的情况。其领导者正在努力改变城市的发展轨迹。然而,尽管匹兹堡拥有前沿的研究和创新潜力,但该地区的大学人才并没有留在这里;我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同事以及我自己的学生纷纷前往硅谷、西雅图和奥斯汀等高科技中心。当互联网先锋Lycos突然宣布将从匹兹堡迁往波士顿时,我脑海中似乎闪过一个念头。
从杜肯山俯瞰匹兹堡Dllu/Wikimedia Commons由于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医疗中心和企业研发单位,以及主要的慈善机构,这座城市能够抵御最糟糕的情况。其领导者正在努力改变城市的发展轨迹。然而,尽管匹兹堡拥有前沿的研究和创新潜力,但该地区的大学人才并没有留在这里;我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同事以及我自己的学生纷纷前往硅谷、西雅图和奥斯汀等高科技中心。当互联网先锋Lycos突然宣布将从匹兹堡迁往波士顿时,我脑海中似乎闪过一个念头。
我在2002年的书中论证,创造阶层的崛起*,*城市成功的关键在于吸引和留住人才,而不仅仅是吸引公司。构成创造阶层的知识工作者、技术人员、艺术家和其他文化创意者正在选择那些拥有大量高薪工作或厚实劳动市场的地方。他们还拥有我所称的厚实交配市场——可以见面和约会的其他人——以及充满活力的生活品质,拥有优秀的餐厅和咖啡馆、音乐场景以及丰富的活动。
我发现自己面对曾经倡导的城市复兴的黑暗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工作在市长、艺术和文化领袖、城市规划者,甚至一些开明的房地产开发商中产生了相当大的追随者,他们在寻找更好的方式来促进社区的城市发展。但我的信息也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引发了反弹。一些保守派质疑我所描绘的多样性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反驳说推动经济发展的不是创意阶层,而是公司和工作。其他人,主要是左派,指责创意阶层和我个人,认为一切从租金上涨和城市更新到贫富差距扩大都是我们的错。尽管一些更个人的攻击让我感到刺痛,但这种批评以我从未预料到的方式激发了我的思考,使我重新构建了关于城市及其所受影响力量的想法。
慢慢地,我对城市的理解开始演变。我意识到,我曾过于乐观地认为城市和创意阶层可以单靠自己带来更好和更包容的城市主义。即使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经历最大复兴的城市中,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随着科技人员、专业人士和富人涌入城市核心,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人和服务阶层成员,以及一些艺术家和音乐家,正被迫退出。在纽约的苏荷,我作为学生观察到的艺术和创意的激荡正让位于一种新的富人、高档餐厅和奢侈商店的同质化。
 2015年,索霍历史区的春街。模糊图像/flickr我进入了一个重新思考和内省的时期,个人和智力的转变。我开始看到回归城市运动是将其好处不成比例地赋予少数地方和人群的事情。我发现自己面对着曾经倡导和庆祝的城市复兴的黑暗面。
2015年,索霍历史区的春街。模糊图像/flickr我进入了一个重新思考和内省的时期,个人和智力的转变。我开始看到回归城市运动是将其好处不成比例地赋予少数地方和人群的事情。我发现自己面对着曾经倡导和庆祝的城市复兴的黑暗面。
当我仔细研究数据时,我看到只有有限数量的城市和大都市地区,也许只有几十个,真正能够在知识经济中取得成功;更多的城市未能跟上步伐或进一步落后。数千万美国人仍然被困在持续的贫困中。几乎所有城市都面临着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随着中产阶级及其社区的消退,我们的地理正在分裂成小块富裕和集中优势的地区,以及更大面积的贫困和集中劣势的地区。
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才和经济资产的同样聚集产生了一种不平衡、不平等的城市主义,其中相对少数的超级城市及其内部的少数精英社区受益,而许多其他地方则停滞不前或落后。最终,推动我们城市和经济广泛增长的同一力量也产生了将我们分开的差距和阻碍我们前进的矛盾。
如果像多伦多这样进步、多元和繁荣的城市都可能遭受民粹主义的反弹,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我对城市和城市主义的看法也深受我在收养的家乡多伦多所看到的事情的影响。我在2007年搬到那里,负责多伦多大学一个新的城市繁荣研究所。对我来说,这座城市是进步城市主义最好的堡垒。多伦多拥有北美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多样化人口;一个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的繁荣经济;安全的街道、优秀的公立学校和紧密的社会结构。然而,不知为何,这座进步而多元的城市选择了罗布·福特作为市长。
虽然他的个人缺陷和功能失调可能让他赢得了福特国的支持者,但在我看来,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反城市的市长。一旦当选,福特就开始拆除几乎所有城市主义者认为构成伟大城市的东西。他拆除了自行车道,并制定计划将城市市中心湖滨的一段黄金地带改造成一个华丽的购物中心,配有一个巨大的摩天轮。
 2009年的多伦多湖滨:原本很好。Wladyslaw/flickr福特的崛起是城市日益扩大的阶级分化的产物。随着多伦多曾经庞大的中产阶级的衰退和旧中产阶级社区的消失,这座城市正在分裂为一小部分富裕、受过教育的地区,集中在城市核心及主要地铁和交通线路周围,以及一大片远离市中心和交通的不利社区。福特的信息在他的工人阶级和新移民选民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们感到城市复兴的好处被市中心的精英所占有,自己却被抛在了后面。
2009年的多伦多湖滨:原本很好。Wladyslaw/flickr福特的崛起是城市日益扩大的阶级分化的产物。随着多伦多曾经庞大的中产阶级的衰退和旧中产阶级社区的消失,这座城市正在分裂为一小部分富裕、受过教育的地区,集中在城市核心及主要地铁和交通线路周围,以及一大片远离市中心和交通的不利社区。福特的信息在他的工人阶级和新移民选民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们感到城市复兴的好处被市中心的精英所占有,自己却被抛在了后面。
我来这里是为了看到这种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如果像多伦多这样进步、多元和繁荣的城市都可能成为这种民粹主义反弹的牺牲品,那么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
当时,我说福特只是这一酝酿中的反弹的第一个信号:更多更糟的事情将随之而来。果然,紧接着英格兰做出了令人震惊且完全意想不到的决定,选择脱离欧盟(即“脱欧”)。这一决定遭到了富裕、国际化的伦敦的强烈反对,却得到了被全球化和再城市化的双重力量抛在身后的工人阶级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挣扎居民的支持。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出乎意料——甚至更加可怕: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特朗普通过动员那些在美国被遗忘的地方的焦虑和愤怒的选民而崛起。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密集、富裕、以知识为基础的城市和近郊,这些地方是新经济的震中,以相当大的优势赢得了普选票。但特朗普赢得了其他所有地方——更远的郊区和农村地区——这为他在选举人团中提供了决定性的胜利。特朗普、福特和脱欧这三者都反映了当今定义和分裂我们的阶级和地理的深刻断层线。
这些政治分裂最终源于新城市危机的更深层次的经济和地理结构。它们是我们这一新时代赢家通吃城市主义的产物,在这种城市主义中,才华横溢和有利条件的人聚集并占据一小部分超级城市,抛弃了其他所有人和地方。新城市危机不仅仅是城市的危机,它是我们时代的核心危机。
局势无法更为严峻。我们如何应对新的城市危机将决定我们是变得更加分裂,滑向经济停滞,还是向前迈进,迎来一个更加可持续和包容的繁荣新时代。
本文改编自 新的城市危机:我们的城市如何加剧不平等、加深隔离,并未能满足中产阶级——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
***更正:***本文中的一段说明错误地将1967年纽瓦克骚乱归因于1968年4月4日发生的马丁·路德·金的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