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在霍乱之后的转变 - 彭博社
Feargus O’Sulliv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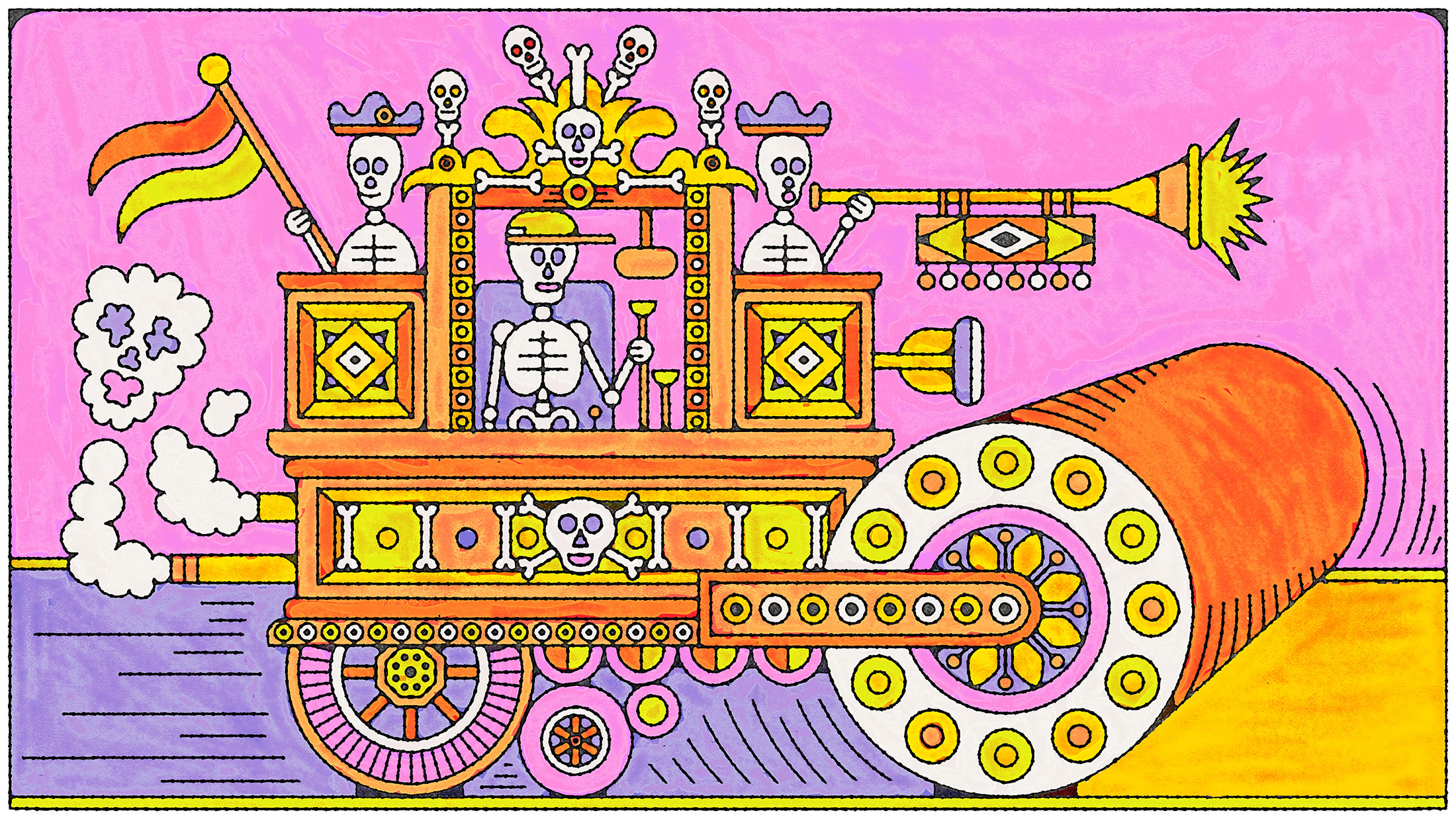 插图:Nolan Pelletier
插图:Nolan Pelletier
(这是三个关于城市及其经济如何从历史性流行病中恢复的故事中的第二个。您可以在这里阅读第一个关于阿姆斯特丹的故事。)
1832年3月,霍乱首次来到巴黎时,一些人拒绝让它影响他们的社交生活。
当时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描述了一个蒙面舞会,就在第一批病例被宣布时举行,舞者们跳着查胡舞,这种高踢的舞蹈后来演变成了康康舞。突然感到寒冷发抖,一个扮演丑角的舞者摘下面具,让人们感到恐惧:他的脸变成了紫色。这是所谓的“蓝色死亡”,由于霍乱细菌在小肠中传播导致极度脱水。一些人笑着认为那是脸上的彩绘,但很快他周围的其他舞者也生病了,并被紧急送往医院。他们死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有些人被埋葬时仍穿着几小时前跳舞时穿的服装。
海涅为一家德国报纸写的这段描述可能是夸大的传闻,但霍乱给巴黎人带来的恐怖以及它传播的速度仍然是真实的。根据《值得捍卫的身体:免疫力、生命政治和现代身体的神化》一书的作者埃德·科恩的说法,这种疾病作为一种来自印度的“殖民地回击”来到欧洲。它是一场全球大流行病,沿着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路线传播,以及它们在南亚夺取的殖民地领土的不断扩大的网络,而霍乱在那里是地方性的。
它很可能通过英国传入巴黎,在公共卫生危机的169天期间,它夺去了18,500人的生命,大约占了该市人口的2%,包括法国总理卡西米尔·皮埃尔·佩里埃。霍乱给那些感染的人带来了迅速而可怕的死亡,也让巴黎的经济陷入停滞。任何能够逃离的人都逃离了,而那些留下的人有时会采取复杂(事实证明是徒劳的)的防护服装来避免感染。这场流行病的压力甚至催生了一场小规模起义,反对法国的新君主立宪制,一小撮叛军在巴黎最受霍乱困扰的地区与军队发生冲突,这一事件后来被记载在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的高潮场景中。
重生计划
这种急性冲击与当今大流行病有令人不安的共鸣,就像17世纪阿姆斯特丹经历的鼠疫一样。然而,最重要的可能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巴黎的霍乱流行病可能造成了严重打击,但正如一项新研究探讨的城市后大流行时期的住房市场所显示的那样,随后出现了迅速的经济复苏。阿姆斯特丹商学院的马克·弗兰克和鹿特丹伊拉斯谟经济学院的马西斯·科雷瓦尔指出,在大流行病期间,房价确实急剧下降,但到1836年,即大流行病爆发四年后,受霍乱影响的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增长恢复到了基本相同的水平。
正如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一样,这种复苏的原因之一是大都市的磁性吸引力,导致逃离法国乡村贫困的移民愿意冒健康风险以获取巴黎的经济机会。该研究还强调了复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场大流行引发了对巴黎规划和建设方式的重大反思。
从狭窄的中世纪小巷组成的不规则城市——难以清洁,容易被1832年的叛乱者等不满分子封锁和设立路障——巴黎被重新构想为拥有宽阔、规则的大道和林荫大道的地方,重新规划以便于市民、交通、士兵和警察、垃圾和污水的流动。通过这样做,巴黎成为了全世界效仿的模板:如何应对撼动城市核心的健康危机最终可能引发有力的重生的典范。
死亡的新地理
巴黎的这种转变部分源自医学研究人员在霍乱大流行之后寻找模式的困惑。政府任命的一个官方委员会审查了有关谁死亡以及在哪里死亡的数据,注意到疾病的传播似乎忽视了当时普遍认为影响传染和死亡的许多因素。在巴黎街道规划图上绘制,死亡人数与受害者的年龄或性别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死亡并没有——正如追溯到希波克拉底的假设可能预期的那样——集中在高海拔或低海拔地区,或者条件明显比平均温度更高、更低或更潮湿的地方。忽略了诸如山脊之类的物理界限和诸如行政区之类的政治界限,官方报告指出,霍乱似乎是有选择性的,只袭击“每四个区中的一个quartier,而在这个quartier中只有一些街道,而在这些街道中只有一些房屋。”那背后是什么呢?
第二组指标使事情变得更加清晰。在这里,研究人员研究了人口密度、某些职业的居住地点、监狱或兵营是否附近,以及至关重要的是,住房是否“不卫生”。这些因素与较高死亡率之间的相关性引人注目:霍乱可能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传染病那样传播,但显然却重创了贫困和居住条件恶劣的人。在巴黎市政厅附近一条众所周知的拥挤街道上,仅有304人死亡。“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说,无论在哪里,只要一个可怜的人口发现自己被困在肮脏、狭小的住所中,那里疫情就会增加受害者。”
贫困与死亡率的联系当然并不是全新的。然而,研究人员的数据确实引发了对城市规划作为卫生措施的新兴兴趣,尽管当时他们尚未完全掌握霍乱的真正原因(细菌通过被污染的饮用水传播),但这很可能改善了公共卫生。
早在1833年,该市开始扩建下水道,总长度增加了14公里 —— 这虽然只是一个小数目,但整体网络却增加了三分之一。在兰布托伯爵的影响下,这一重建工作加快了推进,他在那一年成为了该市的总督,这是现任市长的前身。兰布托承诺给巴黎人民提供“水、空气和阴凉”,大大增加了饮水泉的数量,将煤油灯换成了煤气灯,并启动了一项重新规划城市的计划,他希望能够拓宽街道并改变城市地图。
 尽管进行了一些卫生改进,霍乱于1865年重返巴黎。一幅雕刻作品展示了这种疾病威胁着这座城市。插图:弗朗索瓦-尼古拉斯·希夫拉特(Francois-Nicolas Chifflart),来源:艾尔萨·梅隆·布鲁斯基金会,国家美术馆### 清除地图上的一切
尽管进行了一些卫生改进,霍乱于1865年重返巴黎。一幅雕刻作品展示了这种疾病威胁着这座城市。插图:弗朗索瓦-尼古拉斯·希夫拉特(Francois-Nicolas Chifflart),来源:艾尔萨·梅隆·布鲁斯基金会,国家美术馆### 清除地图上的一切
这种行动可以说既是政治的,也是卫生的。在1801年至1831年间,巴黎的人口增长了近三分之一。在没有城市实际扩张的情况下,这意味着贫困的巴黎人在城市核心区的密度越来越高。在此期间,巴黎(以及法国)的统治者也发生了三次变更,1830年的七月革命将法国确立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这场冲突中,巴黎精英阶层内的一些团体利用这一新扩大的人口的起义力量来推动他们自己的目的。在胜利的阵营中,一些人担心,现在瓶塞被拔掉后,同样的力量最终可能会推翻他们。
因此,要将巴黎摆脱肮脏、不卫生的角落,不仅仅是为了对抗霍乱,还因为对居住在疾病滋生地的不断增长的人群的恐惧。“委员会不得不相信存在一定类型的人口,”1834年的疫后报告写道,“这种人口像某种地方一样,有利于霍乱的发展,使其更加严重,其影响更加致命。”
这些贫穷、易患疾病的巴黎人在当局看来,不仅是疾病最有可能的受害者,还被视为潜在的传染源,可能爆发引起混乱,甚至威胁政治体系。巴黎市中心的重建因此启动了一个漫长而缓慢的低收入置换过程,贫穷的巴黎人从城市的核心地带,也就是主要机构所在地,转移到了周边略微密度较低的社区,比如贝尔维尔,然后后来又转移到今天的郊区。
尽管兰布托总督充满热情,但最初开发巴黎的努力遭遇了阻碍,主要是因为房东的抵抗。城市拆除了塞纳河右岸一处狭窄规划、密集建设的区域,霍乱在那里肆虐,取而代之的是今天的朗布托大街,一条连接马雷区和城市主要农产品市场Les Halles的宽阔街道。在左岸,城市还修建了苏弗洛大街,通过拆除和重建,在巴黎圣母院前创造了一个如今著名的风景。先贤祠。
最初,事情就只进行到这一步,因为当局发现他们的重建计划受到了坚决的征收法律的阻碍,而法院系统主要对房东的上诉表示同情。直到1845年,社会主义者维克多·孔西丹仍然可以称巴黎为“一个腐烂的巨大车间,贫困、瘟疫和疾病共同作用,光线和空气几乎无法渗透。”
考虑到康西丹并没有完全错:1849年,霍乱再次袭击了巴黎,造成的死亡人数比1832年略多。但即使它证明同样致命,巴黎的下一次大流行也确实证实了兰布托的努力。正如弗兰克和科雷瓦尔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他在右岸拆除的区域的死亡率明显低于上一次大流行时的水平。注释。
这一成功,再加上更有力的征收方法,有助于推动下一次更为有效的巴黎重规划,即在19世纪50年代由奥斯曼男爵领导,最终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同心环林荫大道和轴线大街的建筑风貌,以及黄色石灰岩、锻铁和朴素修剪的树木。这几乎不可能被视为一种恐惧的建筑风格,但在其根源中仍然潜藏着一个在舞会上露出病态、发青的脸的冲击。
不作为的危险
在许多城市开始从另一次大流行中复苏的时期,巴黎的迅速复苏可能是令人鼓舞的。然而,在弗兰克和科雷瓦尔的研究末尾,也包括了一项承认,即巴黎的复苏并不一定是一种自动反射。研究指出,伦敦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该城在1854年经历了一次局部且规模较小的霍乱爆发。
这次爆发后来成为传奇,因为流行病学家约翰·斯诺通过对其进行探究成功地确定了霍乱通过粪便污染的水传播:斯诺设法追溯到索霍社区的病例源于一个有问题的水泵。但尽管伦敦爆发的调查推动了医学知识的进步,一篇论文去年发表发现,由于官方不作为,它对受影响地区的改善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尽管伦敦在19世纪后期在卫生和住房条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索霍本身并没有获得明显改善的基础设施。危机之后,它的声誉更加根深蒂固,索霍的租金进一步下降,其庭院和小巷一直保持着贫困和犯罪的声誉,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
巴黎的例子可能表明,在公共卫生危机之后努力思考可以让城市蓬勃发展。然而,就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苏豪区的经历警示着在缺乏有意义的行动的情况下可能会持续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