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会拖延?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用自己的方式工作 - 彭博社
Anna Holmes
 插图:彭博商业周刊的山姆·伍德这个故事是《彭博商业周刊》的特别报道之一。更多内容请点击这里。
插图:彭博商业周刊的山姆·伍德这个故事是《彭博商业周刊》的特别报道之一。更多内容请点击这里。
我最初是怀着最好的意图开始的。坐在沙发上,电脑放在腿上,我开始打字,然后又打了一些字。抬头看到房间对面的情况有点乱,尤其是地板上堆放着一堆书,我买来作为我试图写的书的素材。我站起来把它们整理成更整齐的样子。然后猫在窗边开始哭。我又站起来。原来它想要打开百叶窗,这样它就可以坐在阳光下。我打开了百叶窗。我重新坐下。现在我决定我渴了。但是放在脚下咖啡桌上的一杯番石榴味的LaCroix已经失去了气泡…而且里面还漂浮着猫毛。我站起来打开了一罐新的。在厨房里,我查看了我的Fitbit:到目前为止走了459步——在一个600平方英尺的公寓里。按照这个速度,到下午1点我会走一千步。而现在才早上10点。
 插图:彭博商业周刊的山姆·伍德上一段是我尝试致敬英国作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的——具体来说是他1997年出版的精彩著作《纯属愤怒》,这本书记录了他试图(以及失败、分心和转移注意力)写一本关于D.H.劳伦斯的学术著作。戴尔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逃避写作。他需要更多的报告,需要多做笔记。他不确定自己想住在哪里。在哪个欧洲城市他才能做出最好的作品?(书开始时,他在巴黎,考虑加入他的伴侣在罗马的生活。然后他飞往希腊度假,这并没有帮助解决问题。)他研究雷纳·玛利亚·里尔克的作品,深信“更好地理解里尔克对我理解劳伦斯至关重要。”
插图:彭博商业周刊的山姆·伍德上一段是我尝试致敬英国作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的——具体来说是他1997年出版的精彩著作《纯属愤怒》,这本书记录了他试图(以及失败、分心和转移注意力)写一本关于D.H.劳伦斯的学术著作。戴尔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逃避写作。他需要更多的报告,需要多做笔记。他不确定自己想住在哪里。在哪个欧洲城市他才能做出最好的作品?(书开始时,他在巴黎,考虑加入他的伴侣在罗马的生活。然后他飞往希腊度假,这并没有帮助解决问题。)他研究雷纳·玛利亚·里尔克的作品,深信“更好地理解里尔克对我理解劳伦斯至关重要。”
矛盾的是,他的散文自信而迅猛,表明他并不太在写作上挣扎。此外,在他一本书的早期页面上,在标题“Geoff Dyer的其他作品”下,他的出版商列出了他写的其他10本书。十本!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两本书,而那些只是选集和汇编,不是原创叙事,我想原创叙事比我接手的任何事情都要困难和存在挑战性。直到现在。
我很清楚,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或者说,也不是唯一一个作家——偶尔会遭受无法完成事情的痛苦,有时甚至是病态的。很多作家讨厌写作这个行为。憎恶它。他们有不同的方法来应对这种感觉。有些人散步。抽烟。或者喝酒。当她感到不知所措时,一个朋友使用番茄工作法,设置一个25分钟的计时器,将任务分解成可管理的部分,这样她可以更容易地完成。另一个朋友,Jami Attenberg,即将出版一本名为1000 Words的面向作家的书,副标题是“作家的指南:全年保持创造力、专注力和高效率”。我打算给朋友买几本。
拖延(以及由此导致的缺乏生产力)给经济造成了损失——盖洛普测算出全球“不投入工作的员工”每年造成的成本为7.8万亿美元。拖延会带来明显的个人成本。根据2023年的一项研究,它可能会对你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是一个如此普遍的问题,无论是对作家还是对普通人,都有一个专门的市场致力于帮助人们提高生产力,一种生产力工业复合体。数十本,甚至数百本书,更不用说视频教程、应用程序和网站可以下载和查看或玩耍,都在争夺那些拖延工作的人的注意力。研究人员表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作日用于实际工作。当不在(通常是表演性的)会议中时,人们可能会想象一些时间用于通过拖延来避开令人不愉快且必要的任务。有人可以雇佣来帮助你提高生产力;还有整个贸易协会致力于生产力和组织咨询领域。还有像Tim Urban这样的生产力大师,他的TED演讲“一个拖延狂的思维内部”已经有6700万次观看次数且还在增加。
显然,这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我不想参与其中。谁愿意下载应用程序,听播客,支付顾问费,学习荒谬复杂的日记技巧,总的来说,在很难完成“真正”的工作的情况下花更多的钱呢?
但是,我的书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要交稿了,我写了大约25,000字,而我希望写的是这个数量的四倍。我需要一些帮助。所以我决定做我知道自己擅长的一件事,阅读书籍,既能理解自己的拖延行为,又能在与其他拖延者一起感到稍微不那么孤独。
 插图:Sam Wood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奇怪的是,我目前的情况相当新颖。多年来,我一直是一名作家和编辑,之前还有两本书问世。一本是关于女性分手信的文化史;另一本是一本百科全书,受到我创建的名为Jezebel的网站观点的影响。我没有拖延这些书,老实说,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一个想法:随着我成为一名更有经验的作家,我也变得更加不安全,被一种在年轻时没有的冒名顶替综合症所束缚。 (稍后详谈。)另一个:我只是变得更老和更懒。第三个:该死的互联网的干扰。
插图:Sam Wood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奇怪的是,我目前的情况相当新颖。多年来,我一直是一名作家和编辑,之前还有两本书问世。一本是关于女性分手信的文化史;另一本是一本百科全书,受到我创建的名为Jezebel的网站观点的影响。我没有拖延这些书,老实说,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一个想法:随着我成为一名更有经验的作家,我也变得更加不安全,被一种在年轻时没有的冒名顶替综合症所束缚。 (稍后详谈。)另一个:我只是变得更老和更懒。第三个:该死的互联网的干扰。
这个项目也是我承担的一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我可以向学员和其他人强调,恐惧是工作中的重要部分,我们需要做那些让我们感到害怕和挑战的事情,才能在事业和其他方面取得进步和上升。但是独自写书的工作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快速沙漠中挣扎。在我职业生涯的其他时候,例如当我为一个更大的实体担任编辑,并且还有一个办公室工作时,我没有拖延的问题。事实上,以前的同事可能会说我有过度工作的问题,经常对我的健康和个人关系造成损害。
现在?有人可能会说我正在过着梦想般的生活。我可以在家工作。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决定何时洗澡。 (通常我会洗。)但作为编辑、创意总监或制片人与创意型人才合作是一回事。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出视线,帮助其他人闪耀。写作,尤其是写书,是另一回事。首先,我的名字会出现在封面上。我还有经济责任——其中很多是对我的父母,他们从未赚过多少钱——这些责任令人难以承受,而且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无结构的时间和内在压力要制定一个固定的时间表,让我以前从未有过的方式来评判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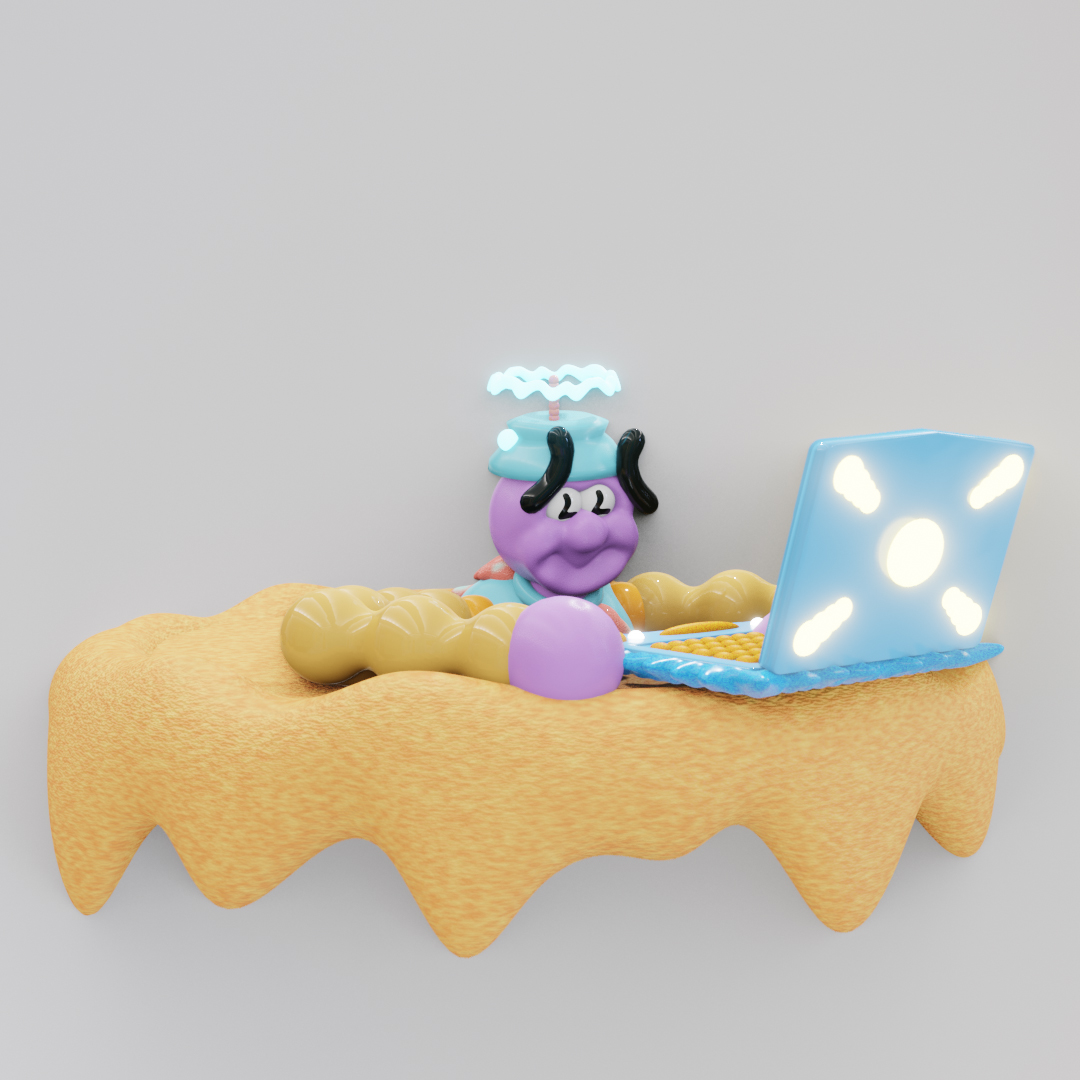 插图:彭博商业周刊的山姆·伍德我的新书的主题是我不想谈论的事情。从一对新书中我学到,不谈论它,是从凯瑟琳·摩根·施弗勒(Katherine Morgan Schafler)的《完美主义者的失控指南》和托马斯·柯兰(Thomas Curran)的《完美主义陷阱:拥抱足够好的力量》中学到的,这是一种完美主义,一种控制似乎失控情况的方法。毕竟,如果我不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那么它的不可避免的失败——或者甚至是我无法完成它——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至于完美主义,根据柯兰这样的专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以及心理治疗师施弗勒的说法,它是拖延的根源,如果不是根本原因。
插图:彭博商业周刊的山姆·伍德我的新书的主题是我不想谈论的事情。从一对新书中我学到,不谈论它,是从凯瑟琳·摩根·施弗勒(Katherine Morgan Schafler)的《完美主义者的失控指南》和托马斯·柯兰(Thomas Curran)的《完美主义陷阱:拥抱足够好的力量》中学到的,这是一种完美主义,一种控制似乎失控情况的方法。毕竟,如果我不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那么它的不可避免的失败——或者甚至是我无法完成它——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至于完美主义,根据柯兰这样的专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以及心理治疗师施弗勒的说法,它是拖延的根源,如果不是根本原因。
Schafler的书以一个简短的测验开始,帮助读者确定他们属于五种完美主义者中的哪一种。我参加了测验,很快发现自己一半是巴黎完美主义者(具有强大的同理心和与他人建立紧密联系的强烈愿望),一半是凌乱完美主义者(一个“超级创意生成者”,不能始终专注于目标)。奇怪的是,我显然不是拖延狂完美主义者,这种类型的人经常反刍,预期失败,淡化自己的成功,开始任务时会“等待条件完美才开始”。这对我来说感觉不公平,除了等待条件完美才开始。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但反刍和其他一切呢?经典。为了超越他们身份的这一方面,Schafler建议拖延狂完美主义者“与支持者结盟”。这既有点模糊,又违背了我在感到害怕和困惑时通常会做的事情,那就是躲在某个角落里,是的,反刍。
《完美陷阱》中没有测验,这本书强烈主张拖延是完美主义的症状。正如Curran指出的那样,“完美主义者将拖延作为一种在没有必然情感伤害的情况下度过挣扎、挑战和失败的方式。”当我在七月中旬通过电话与Curran交谈时——一开始电话打不通,这让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宽慰——他将拖延描述为情绪调节问题,而不是时间管理问题。
情绪调节,意味着练习并掌握对困难情绪状态的控制,这是我几年来一直在努力的事情。我的治疗师作为认知行为疗法课程的一部分,敦促我在感到焦虑或不安时“观察和描述”。她说这既可以让我平静下来,也可以处理我的情绪。但当我拖延时,我感到无法完全观察或描述任何事情,因为我感到的是彻底的、压倒性的羞耻。一位知名的TikTok博主@neuroqueercoach也提供了类似的建议,向她的粉丝解释说拖延是一种“我们可以通过意识到我们拖延时的情绪来改变的习惯。”但至少对我来说,观察和描述似乎会促使我感到更多的羞耻,然后导致更多的恐惧、厌恶,毫不奇怪,更多的拖延。
对于我自己大脑之外的人来说,“羞耻”可能感觉有点言过其实。有点太戏剧化了。然而,它似乎也是恰当的。柯兰本人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个词。在他的书中,这位自称完美主义者早早地解释说,他的治疗师“能够向我展示,我正在遭受深刻的自我厌恶、羞耻和悲伤,这些情绪被我的完美主义者身份巧妙地掩盖和加剧。”在我与他的通话中,柯兰说完美主义者发现很难处理失败,并与“强烈需要他人认可”的情绪斗争,这导致了深深的羞耻感。当事情变得困难或当他们面临他们确信会失败的任务时,他们会退缩、反刍并参与“自我破坏”的拖延。这是一种焦虑管理技术——正如柯兰所说的“非常强大的材料”。而且真的很糟糕。
 插图:彭博商业周刊的山姆·伍德虽然柯兰(以及纽约时报)强调拖延是关于情绪,而不是时间管理,但我并不急于否认这个想法,即它并没有受到现代时间压力的深刻影响。时间是珍妮·奥德尔(Jenny Odell)精彩新书《 拯救时间:发现时钟之外的生活》的主题。巧合的是,正是在我将那个代表优化的硅谷标志,一只苹果手表,绑在左手腕的时候,这本书到手了。
插图:彭博商业周刊的山姆·伍德虽然柯兰(以及纽约时报)强调拖延是关于情绪,而不是时间管理,但我并不急于否认这个想法,即它并没有受到现代时间压力的深刻影响。时间是珍妮·奥德尔(Jenny Odell)精彩新书《 拯救时间:发现时钟之外的生活》的主题。巧合的是,正是在我将那个代表优化的硅谷标志,一只苹果手表,绑在左手腕的时候,这本书到手了。
奥德尔认为,现代时间观念与工资劳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实密不可分,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对于人类意义的看法。这似乎与我身上戴着的设备的用意背道而驰,因为它可以显示互联网时间、温度和日期。(更不用说它计算从我的血氧水平到我从坐姿站起的频率的一切。“该站起来了!”它欢快地宣布。)
更多来自商业周刊的特别报道:
我对此感到奇怪。不仅仅是因为我购买了我实际上不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看着我的预付款减少时感觉自己在花钱。 (我安慰自己,我的苹果付款计划让我每月只花费32美元。)也不是因为购物本身就是一种拖延或情绪逃避的形式。而是因为,正如奥德尔指出的那样,特定时间点的概念和规范(她称之为“时间单位”)是一个相当近期的现象,源自于,并且使时间被视为金钱的想法得到了实体化和强化;一种可以量化、利用的东西。这也非常白人化。奥德尔引用了学者布里特尼·库珀(Brittney Cooper)2017年的TED演讲,“时间的种族政治”,这是对库珀解释的“权力者如何规定工作日的节奏…他们规定我们的时间实际价值有多少钱”的引人入胜的探索。
奥德尔的书没有涉及拖延。至少不是明确地。但它也没有必要。正如她所指出的,我们将时间用作繁忙程度的衡量标准,也被用作衡量谁和什么是“好”的标准,谁“赢了”或“压倒了”的标准。我意识到,我的苹果手表只是另一种主要用途是测量我如何使用或不使用我的时间,计算我在生活游戏中表现如何的设备。我想起了书中的一个早期部分,奥德尔在日记中分享了她的思考,特别是她在从东湾到旧金山半岛的汽车上的观察。 “在绿灯亮之前,我低头看着我的手机,它在旧杯架里格格不入,”她写道。“一个伴侣,是的,但也是一个衡量生活的设备。”
奥德尔特别痛恨自助和时间管理书籍,以及她所称之为“生产力兄弟”,这些平凡无奇的家伙们具有“自我掌控的修辞,为YouTube和Instagram时代重新打造而成”。当你寻求克服拖延的帮助时,你可能会遇到这些生产力兄弟,像Urban这样的人,他将2016年的TED演讲转化为更多关于拖延和生产力的内容,以及亚当·格兰特,一位组织心理学家和TED的同行,他有五本畅销书籍涉及拖延相关主题,比如动机。互联网的大片区域被那些给出生产力建议的男性占领了——如何崛起和奋斗,保持努力,永远不要让目标离眼前,保持专注。他们只痴迷于一件事,那就是不浪费时间。
奥德尔提到的另一个人是克雷格·巴兰丁,他自称为“世界上最有纪律的人”,2015年几乎在凌晨4点起床工作,写作了他的著作完美的一天公式:如何拥有美好的一天并掌控你的生活。凌晨四点!
我决定我讨厌克雷格·巴兰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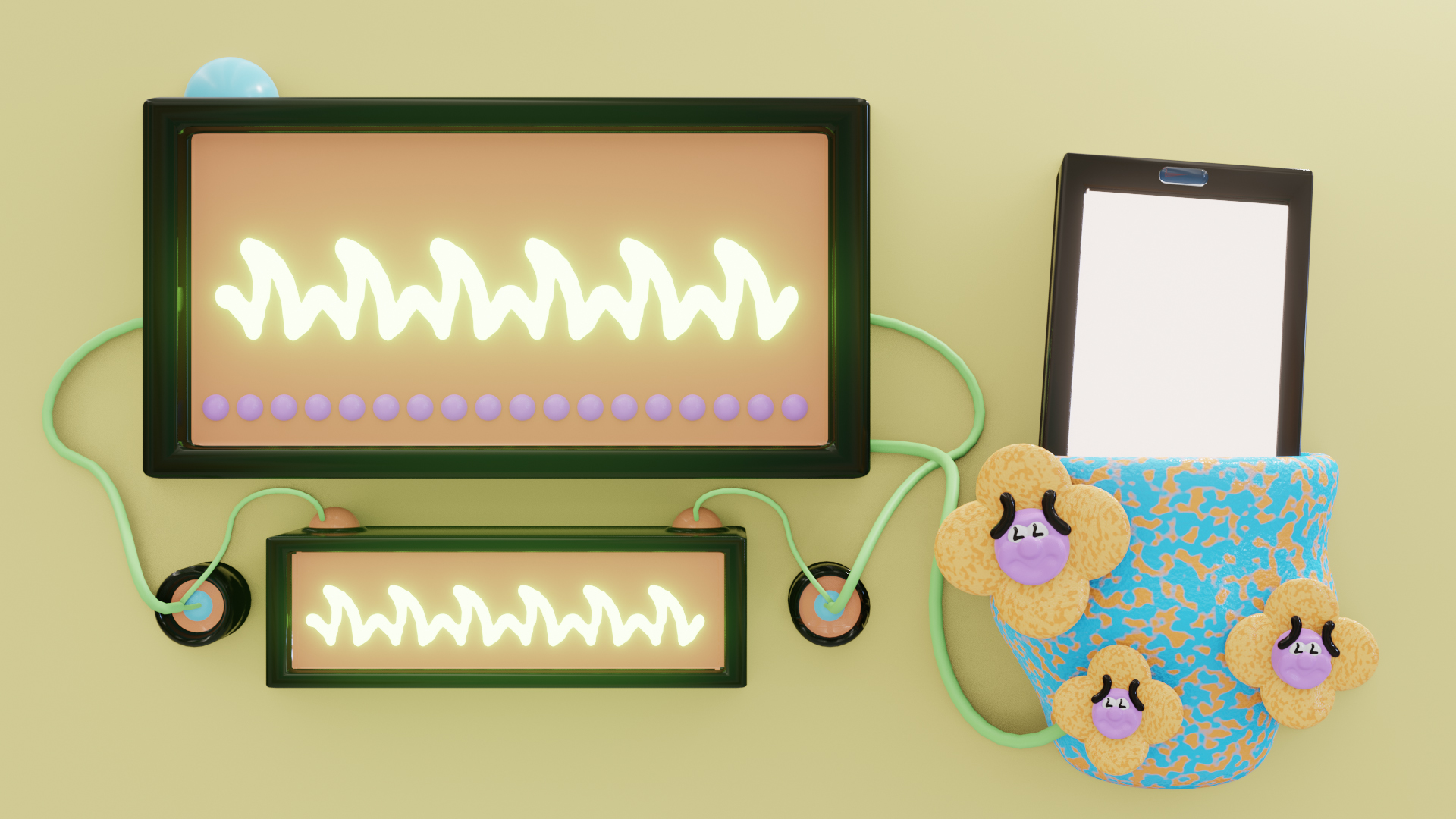 插图:彭博商业周刊的萨姆·伍德我有时会思考完美主义与性别和种族巨大压力之间的联系。对于许多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群来说,成为“最好的”——或者比最好的更好——是获得机会的先决条件。2018年,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完全披露:我曾为她的制作公司Higher Ground工作)在她的超级畅销书籍 成为中提到,“你必须做到比别人好一倍才能走得更远。” 奥巴马本人也在回应黑人美国人之间经常表达的观念,即他们必须做到比白人同行更优秀才能获得更容易被我们白人同行享有的职业利益和尊重。
插图:彭博商业周刊的萨姆·伍德我有时会思考完美主义与性别和种族巨大压力之间的联系。对于许多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群来说,成为“最好的”——或者比最好的更好——是获得机会的先决条件。2018年,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完全披露:我曾为她的制作公司Higher Ground工作)在她的超级畅销书籍 成为中提到,“你必须做到比别人好一倍才能走得更远。” 奥巴马本人也在回应黑人美国人之间经常表达的观念,即他们必须做到比白人同行更优秀才能获得更容易被我们白人同行享有的职业利益和尊重。
这种压力是我能够理解的,作为一个来自中下层家庭的黑人,也是一个女性。多亏了我家乡的公立学校系统,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我也很早就意识到,要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特别是在纽约媒体的白人和男性主导的常春藤联盟领域,我必须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专注和强度。我需要假装直到成功。
柯兰(Curran)也在一个中下层家庭的环境中长大,并且通过大量的努力和辛勤工作,一步步攀上了学术阶梯。尽管他的书并没有深入探讨种族和性别在完美主义中的作用(也许作为一个白人男性,他不是合适的人选),但他谈到了阶级,包括自己和他人的阶级。“当然,我自己与完美主义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需要过度成就,以弥补社会和经济力量不断对我施加的影响,”他写道,使用现在时。
 插图:彭博商业周刊的Sam Wood有一种特定的羞耻和自我厌恶的简称,滋养着拖延工作的习惯,当我们逃避工作以避免失败时:冒名顶替综合症。毕竟,如果我不是别人认为的那个人,如果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我被揭露的威胁——所有那些公开曝光和尖锐批评——都表明我根本不应该尝试。(我已经预料到,带着恐惧,我未写的书在 Goodreads 上的评论。)
插图:彭博商业周刊的Sam Wood有一种特定的羞耻和自我厌恶的简称,滋养着拖延工作的习惯,当我们逃避工作以避免失败时:冒名顶替综合症。毕竟,如果我不是别人认为的那个人,如果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我被揭露的威胁——所有那些公开曝光和尖锐批评——都表明我根本不应该尝试。(我已经预料到,带着恐惧,我未写的书在 Goodreads 上的评论。)
有一位作家在应对 冒名顶替综合症 这个术语的流行和其多重含义时,是莱斯利·贾米森(Leslie Jamison),她在二月份的一篇 New Yorker 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像奥德尔的书一样,贾米森的文章没有明确提到拖延,但其描述人们为了避免被发现自己所认为的失败而不遗余力的行为,与我所读到的关于拖延者为何这样做的内容很相似。
“冒名顶替者开始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发现她所有自我感知的缺陷,” 贾米森写道。她写道,一些女性“对自己的悲观主义采取了一种魔法般的想法:敢于相信成功实际上会注定他们失败,因此失败必须被预期。” 或者,如果不是被预期,那就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
一些人说,冒名顶替综合症的概念—就像时间的概念—非常白人化。贾米森,一位白人,提到了2021年《哈佛商业评论》中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别告诉女性她们有冒名顶替综合症。” 文章的作者,贾米森指出,“认为这个标签意味着女性正遭受自信危机,而未能认识到职业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所面临的真正障碍—本质上,这将系统性不平等重新框定为个体病理。”
Jamison 还引用了一些人的话,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繁荣是建立在女性患有“综合症”自我怀疑和自尊低下的概念之上的焦虑之中。 “感觉像个骗子确保我们会为无尽的进步而努力:更加努力工作,赚更多钱,努力比我们以前的自己和周围的人更好,” 有人告诉 Jamison。 这种情绪在 Jenny Odell 的书中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拖延可能只是骗子综合症的一个症状,当然不是最糟糕的一个,但是避免失败的根本动力可能会对女性产生毁灭性后果,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在 Lisa Damour 的 2019 年著作中, 压力之下,这位畅销书作者和临床心理学家谈到了一群女孩的流行病,她们对完美主义的执着使她们生病。 “在极端情况下,一些女孩决定只有在工作‘完美’时才能放松,” 她写道,并补充说 “过度准备” 有助于缓解焦虑并赢得父母、同龄人和老师的赞赏。 “对于受到恐惧驱使的学生来说,这个系统非常有效。直到变得不可持续为止。” 并不是说青春期对我来说很容易,但至少我和我的同龄人没有受到关于课外活动或从 10 岁起就要进哈佛的压力。 (我是X世代的一员,尽管我们被指责懒惰,但在当前完美主义的氛围中,我会说我们在成长时期很幸运。)
 插图:Sam Wood为彭博商业周刊绘制几周前,我联系了杰夫·戴尔本人,想和他谈谈他的书和他的写作过程。他有点像一个偶然的拖延先知(《纽约客》称《纯属愤怒》为“一个避免拖延的经典”,而《Bookforum》则认为这就是写拖延应该看起来的样子,因为这就是在其甜蜜、让人瘫痪的海洋中溺水的感觉),但听到他写那本书的过程对他来说既容易又有趣并不让我感到惊讶。他说他没有“写作障碍”,尽管他确实有时会拖延,有时甚至要过几个月,甚至整整一年,才认真开始写一本书。
插图:Sam Wood为彭博商业周刊绘制几周前,我联系了杰夫·戴尔本人,想和他谈谈他的书和他的写作过程。他有点像一个偶然的拖延先知(《纽约客》称《纯属愤怒》为“一个避免拖延的经典”,而《Bookforum》则认为这就是写拖延应该看起来的样子,因为这就是在其甜蜜、让人瘫痪的海洋中溺水的感觉),但听到他写那本书的过程对他来说既容易又有趣并不让我感到惊讶。他说他没有“写作障碍”,尽管他确实有时会拖延,有时甚至要过几个月,甚至整整一年,才认真开始写一本书。
他承认有一种恐惧,随着年龄增长似乎变得更糟。 “当你年轻时,写你的第一本或第二本书时,感觉真的很棒,”他说。“‘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写这本书将使我成为一名作家。’”戴尔说。但后来,他说,当所有写书的工作变得清晰时——“知道所有这一切工作的感觉——人会感到一种恐惧。”
这让我想起我最近和一位建筑师朋友的一次对话。他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他为好莱坞山丘的一位成功的剧本医生和电视编剧(《辛普森一家》的创作者之一)设计了一个10英尺乘10英尺的“作家塔”。该塔包括两个阳台,这样作家就可以打开塔的玻璃门,享受20英尺的空间,可以在里面来回踱步,试图解决他写作中的问题。塔内还有一张小床供小睡。
这是他第一次说,他明白拖延可以被融入创造过程中——实际上必须被融入其中。“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就是它的本质,”这位建筑师说。“拖延是一种避免的方式—一种深深人性化的避免方式—避免制造丑陋的极端痛苦。”
同样,戴尔正在进行一个关于他童年的项目,他说他会做任何他能找到的事情来打发拖延的时间:家务,打网球等等。然后,最终,他开始了。在这一点上,他尽力接受拖延是过程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极其低效的进行方式,但我似乎被困在其中。”
“到了一个地步,我发现不做比做更加无法忍受,”他补充道。
我开始有共鸣了。我的苹果手表震动了。该站起来了。